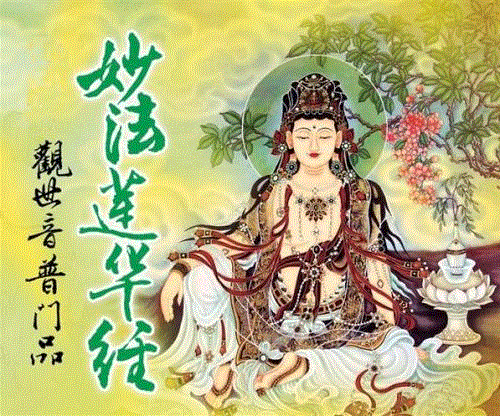三、《起信论》与唯识学的会通<?xml:namespace prefix = o ns = "urn:schemas-microsoft-com:office:office" />
《起信论》以如来藏思想为主,但糅有唯识思想。如在生灭门中,无明作为近因(直接因)缘起诸法,即由不达一法界,而有不觉妄心生起。一切杂染诸法皆是妄心的妄念。心生种种法生,心灭种种法灭。故《起信论》云:“三界虚妄,唯心所作。”[18]唯识学以唯识思想为主,亦有如来藏思想,如上节所述。故二者虽立意有别,但还是相容的。二者的会通,关键在于基本概念含义的比较。 (一)一心的体用相摄与唯识的性相不离 《起信论》“一心”的“心”虽名为众生心,但既不是心性、如来藏,也不是能缘虑的心,是一总相,总括一切诸法。心开为二门,以真如为体,生灭为用,二者不即不离。从真如门观,一切皆是真如,以真如体摄生灭用,此心可称真(如)心;从生灭门看,一切皆是生灭,以生灭用摄真如体,此心则称生灭心。 在唯识学中,与“一心”相对的是“唯识”。此“唯识”摄一切所知境界,即一切法,包括有为与无为法。而识为相[19],无为法为性,二者不一不异。由此,唯识亦可开为二门,所谓相门及性门,二者各可摄一切诸法。但唯识学主要谈相门。 在“一心”中,“一”是“即”义,而“唯识”中的“唯”非“即”,是“不离”义。故心不同于识,识相当于生灭心。又,前者以真如为体,生灭为用,体用相摄;而后者以识为相,无为法为性,性相不离。相摄者,以体摄用,成真如门;以用摄体,立生灭门;由于真如亦是性,体用相摄就是性相相摄。不离者,以相摄性,成唯识门,但没有以性摄相的性门;且真如既不是体,也不是用,性相构不成体用关系[20]。(见表六) “一心”摄一切法,“唯识(唯心)”亦摄一切法,显然“一心”与“唯识”(唯心)相应,而且都可开为二门,只是二者强调的重点不同。由佛果是真如(如来藏)的圆满显现,《起信论》以无为法真如为根本;由佛果是染法的无余灭尽所显,唯识学以有为法识为根本。唯识学整个就是相门,与之相应,《起信论》的相用门是生灭门。此二门都直谈有为法,而且都认为三界是虚妄染心的造作,直接的根源是无明。区别在于,唯识学以阿赖耶识为根本依谈缘起,而真如只是疏助依(缘),没有揭示出阿赖耶识在流转时对真如的覆障作用,也没有表明真如是还灭的内在原因和可能性。《起信论》以真如为根本依,无明为生灭依,就解决了这个问题。但《起信论》在有为法的互熏缘起上,也没有唯识学讲得那么精深。二者实际上各有侧重。唯识学以唯识思想为主,也涉及了如来藏思想,不过没有将之与唯识糅成一个整体。《起信论》以如来藏思想为主,糅有唯识思想,但没有展开。这可从两者共同宗奉的经典《楞伽经》可以看出。《楞伽经》实际上包含了如来藏思想与唯识思想这两方面的内容。唯识学和《起信论》分别代表了其中一方面的发展与完善。唯识学将其唯识思想发挥至极,以如来藏思想副之;《起信论》则将其如来藏思想阐扬净尽,而糅入唯识思想。二者其实是互补的,并不矛盾。 (二)真如与如来藏 真如义与熏习义是《起信论》论争的两个焦点,对《起信论》的责难也导源于此。先来谈一谈真如。 在唯识学的传统诠释中,二无我所显的真如是凝然的理性[21],很明显支持真如门中之真如义,以及生灭门中的“自性相”义。但对生灭门的“随缘”义,情况就要复杂一些,争论也大多发生在这里。“随缘”义意味着真如参与了缘起,而且非是疏助缘,是根本依(因)。唯识学者对此是难以接受的,从唐代的智周法师,到近代的欧阳竟无居士等,都有置疑、批评乃至否定。唯识学反对不平等因,要求因果平等,即果若是有为法,生果的因亦当是有为法。而在“随缘”义中的因是恒常不动的无为法真如,果却是有为法,故被指责为悖理,如王恩洋居士说此所立真如是不平等因,是能生、是唯一因、是常法[22],坏真如法及缘起法;更说此真如是实有物,如同数论之“自性”,是外道法;另外,唯识学中染净不能互熏,不能互为亲因果,而在“随缘”义中,真如与无明杂染互熏,互为因果,亦乱了缘起法。简而言之,就是“背法性,坏缘生,违唯识。”在随缘义中,如果真如被释为能生自果的种子式的亲因,及真如与无明互熏满足唯识学的熏习义,则这些批评是正确的。但事实上,如前第二节已述,真如作为如来藏在随缘义中根本不是种子式的亲因,而且,真如与无明互熏亦不满足唯识学的熏习义,是用真如作为如来藏的在缠义来说明真如随缘的。故上述批评是无的放矢。 除了部分唯识学者持批评态度外,中国佛教学者一般认为随缘义是理所当然的。辩护者约有三类:立场与唯识正相反对者;认为与唯识相容者;及欲以唯识诠释者。 第一类是态度最强硬者,根本反对任何对《起信论》的批评。如守培法师批驳唯识学以无性之性为实性,认为这相当于说龟无毛,无毛之毛是龟的真毛。真如不是无性之性,是实有物,而余一切法皆是假法。只有作为实有物,真如才能是体,才有用;否则,就如同说无皮有毛一样。而且,正因为真如是实性,它才可以作因,生余一切法。他进一步批评唯识学的熏习等许多观点,认为只有相反之法间,比如无为法与有为法间、净法与染法间,才能互熏,毫无疑问,真如与无明可以互熏等[23]。他的这些说法有一定的代表性,但基本上是错误的。首先,唯识学说真如是无自性之所显者,无(自)性是唯遮,表自性定无,但无自性之所显却非无。又,真如是共相,而相与性常通用,真如是无自性所显之共相,可说成无自性所显之性,有时简称无(自)性之性[24]。由此,无性之性并非如无毛之毛。其次,真如是离言之性,而称实性,非是实有物,亦不能作亲因生一切法;否则,真如就同数论之自性、印度教的大梵,而成外道法。至于熏习,将在后面述及熏习义时再批评。 大多数佛教学者持第二种立场。他们认为《起信论》的义理与唯识学的确有不同之处,这些不同之处不能用唯识学来解释,但亦不与唯识学矛盾,而且正是这些不同之处表明《起信论》超过唯识学。唐代的元晓法师(新罗人)、法藏法师等持有这种观点。他们同意真如随缘义成立,但不认为恒常不动的无为法真如能生有为法,需找到一个新的诠释思路。元晓法师认为,真如与生灭二门的真如义不同。真如门之真如是常住之理,假立真如、实际等名;生灭门之真如,理体虽离生灭相,但亦不守常住之性,随无明缘流转生死,自性清净,假名佛性、本觉、如来藏等。此中,“不守常住之性”义指真如可随缘作缘起之亲因缘。法藏法师亦认为真如随缘,即是真如“不守自性”义。这样,生灭门的真如既非常住之理,亦非有为法,而能受熏及作亲因缘,不同唯识中唯有为法方能受熏及作亲因缘,故称真如受熏为不可思议熏习,真如缘起是不可思议缘起[25]。而且认为不思议熏习与缘起虽不能用唯识学的有为法的相熏与缘起来解释,但也不与之矛盾。这种辩护还是不能令人信服。如果生灭门的真如既非无为法,又非有为法,就越出了有为与无为二分的范围,成为一种非有为非无为之法,这不就成了象小乘犊子部不可思议我那样的法吗?又真如之理湛然常住、如如不动,岂有不守自性之理?

此说在逻辑上有矛盾,在义理上有困难,更谈不上与唯识学相容了。故试图用“常”与“不守常住之性”二义区别二门真如,以解释真如随缘,也不成功。 第三类佛教学者深受唯识学影响,又承认《起信论》的义理,而且认为《起信论》不仅不与唯识学矛盾,甚至可用唯识学来诠释。他们一方面避免以无为法真如为因、果,如陈维东强调无为法真如是体,一切有为法是用,无为法真如与一切法不构成因果关系[26];另一方面认为清净有为法与真如是因果关系。为此,在真如随缘问题上,他们将真如的含义扩展到清净有为法,认为唯识学谈真如偏重理性方面,而实际上真如不仅有理性,还包括正智、无漏种现,乃至一切清净有为法。另外,熏习义一般不取唯识亲因果的熏习,而是有漏与无漏间的增上缘关系。太虚大师就认为真如既有理性,亦含正智。而此真如与无明互熏,非是唯识的亲因果的熏习,而是作为增上缘相互影响[27]。故真如影响无明而有净法生起,无明影响真如而有染法生起。在陈维东那里,真如还含一切无漏种、现,即一切清净有为法。在真如与无明互熏中,将真如理解为清净有为法,并以无漏种、现为主再将真如一分为二。无明熏真如中,真如指无漏种及依无漏种所具之净功德;而在真如熏无明中,真如指无漏教及依无漏教所起之闻思修[28]。唐大圆认为真如有遮遍计所显者,还有表依他如幻而显者。真如与无明互熏非是现行熏种子,多是现行相熏,即增上缘关系,故可有有漏与无漏的相互影响,即相熏[29]。这类观点提到真如不仅有常住的理性,而且包括清净有为法,这是对真如义的正确把握。但是,他们在解决随缘义时,太注意相熏必在有为法间发生,以避免与唯识学矛盾,结果得出了熏习主要是有为法间的增上缘关系的错误结论。要知道,真如与无明互熏,核心是无为法真如与无明妄法间互熏,非是清净有为法真如与无明妄法互熏,如“真如自体相熏习”。而且,如果熏习是增上缘关系,则无法说明定有真如熏无明而起净法不断,及无明熏真如而起染法不断。因为,增上缘可引生净法,亦可引生染法,是不定的,不象亲因种子必引自类果。而且,在《摄大乘论》等唯识学经典中,已经反复论证了增上缘关系不能成立熏习的道理,这里不赘述。 前述对待《起信论》的四种立场,虽然结果都不能令人满意,但因其出发点不同应得到不同评价。前两种的观点、态度都比较偏激,蔽于一端;而后两种采取调和圆融的态度,认为《起信论》与唯识并非水火不相容,试图在二者间搭桥。实际上后两种处理方法就是会通,虽然结果并不令人满意,但其努力还是可嘉的。笔者认为,调和圆融应是对待《起信论》与唯识学间关系的基本立场,因为《起信论》属于如来藏系统,与唯识学相涉,毫无疑问应该相容。 根据前面第二节所谈的唯识学的真如义,唯识学的真如义与《起信论》的真如义是完全一致的。真如由离二我执,得名真如,偏重谈恒常不动的理性;真如由具足一切如来净法,得名如来藏,偏重谈虽是常理,而含摄一切清净法。在王恩洋居士对《起信论》的批评中,只注意到真如离分别、恒常的理性义,称之为“空相、空性、空理”[30],没注意到真如含摄净法的如来藏义。如来藏有在缠与出缠义,相应于真如,就有真如覆(有)垢障与离垢障之义。如来藏在缠,就是真如为杂染垢障所覆,就是所谓的真如随缘,也就有了真如与无明的互熏,即如来藏与无明不一不异的相摄关系,由此成立流转与还灭的过程。太虚大师等虽注意到真如含摄一切净法义,但没有辨明真如随缘(或真如无明互熏)主要说明的是如来藏随缘(或如来藏无明互熏),其中虽然亦有清净有为法的熏习,但决非单是清净有为法(如无漏种现、如来教法等)与无明染法的关系。 总而言之,由于唯识学的真如不仅是理性,而且含摄一切净法,故可释为如来藏,这样,真如(如来藏)随缘的道理就与唯识学不矛盾了,而且真如(如来藏)、无明间的熏习与有为法间的熏习正好成为互补。这在后面将进一步解释。 (三)熏习与缘起 如同唯识学一样,《起信论》亦以熏习成立缘起,但其熏习义引起了很大的争议,成了部分唯识学者否定《起信论》的依据。《起信论》中的熏习有二:顺染法熏习与顺净法熏习。在此中引起批评的是无明熏真如和真如熏无明二义。这里出现了几个问题:熏习只能发生在有为法之间吗?无明与真如能互相熏习吗?如果能熏,如何熏? 在唯识学中,熏习只涉及有为法,能熏、所熏、习气(种子)皆是有为法,而且,染法与净法间不能互熏。《起信论》熏习的定义,似乎也支持唯识的说法。在它的花熏衣服的比喻里,有能熏、所熏及所熏留之香气。这表明《起信论》的熏习亦具三相,皆是有为法,王恩洋居士就是这么认为的[31]。然而《起信论》在具体谈到真如与无明互熏时,似乎变换了含义:有为法与无为法,染法与净法,可互相熏习。这与唯识学的熏习道理肯定是相违的,唯识学者当然予以否定。这对维护《起信论》者也构成了一个巨大的困难。于是,守培法师等就干脆否定唯识学的熏习义,认为正因为真如是无为法,是唯一真实物,才能熏习有为法,生起有为法[32],但这确实带来了“常能生变”的不平等因等问题,不仅在唯识学中,在中观学中也曾反复给予遮遣。因此,对会通者而言,必须在与唯识学相容的前提下,进行重新解释,以成立真如无明互相熏习的道理。 首先,他们赋予熏习更宽泛的含义。在《起信论》的熏习喻中有花、衣服及残留香气,如果一一对应,则熏习必如唯识所说具三相,即能熏、所熏和习气种子。但他们认为,正如《瑜伽师地论》所说,喻和所喻不必完全相合,只需部分相合即可[33]。换言之,《起信论》的花熏衣服所喻的熏习,可以不立习气种子,而只立能熏与所熏。这样,由于不需种子习气,熏习的能熏所熏就不必同时,而且,也不必能熏是净或染法,所熏是无记法,甚至能熏所熏不必都是有为法。太虚大师、常惺法师、唐大圆、陈维东等就这么认为,但他们保留了能熏所熏是有为法的要求。这种熏习反映的是一种增上缘的关系,当然不会与唯识学要求的熏习必在有为法间的大原则相矛盾了。这就是他们会通真如无明互熏的基本思路。循此路线,真如就不能唯诠释为无为法,而应包括清净有为法。即真如包含一切净法,如正智、无漏种现、一切如来教法,如前小节所述。在真如无明互熏义中,真如进一步被释为清净有为法义。由此可得出结论:真如与无明互熏,是清净有为法与无明杂染法的互熏,形成了相违的增上缘关系。由于增上缘的关系可以有顺益与违损两种,真如与无明互熏就是一种违损性熏习。对此,太虚大师具体解释道,二者互熏就是有漏无漏相违间杂而生[34]。此中更有区别:唐大圆认为,熏习指现行间的关系,“有漏现行与无漏净法(现行)相违反故,有因无明熏而有染相,因真如熏而有净用也”[35],太虚大师亦同此见;陈维东却认为亦应包含现种间的熏习,真如熏无明指无漏教及依无漏教所起的闻思修熏有漏异熟与一切染种,无明熏真如指一切戏论及有漏现行熏无漏种及依无漏种所具之净功德[36]。 但增上缘的关系是不能解释真如与无明互熏的缘起的,主要有两点理由:第一,违反《起信论》中的缘起道理。《起信论》明确指出,无明熏真如而起染法不断,真如熏无明而起净法不断。如果在真如与无明互熏而缘起的因果关系中,仅是增上缘关系,不能保证无明熏真如生起染法,亦不能保证真如熏无明生起净法。因为增上缘可顺可违,同样的增上缘可使净法生起,也可使染法生起,如同阳光既可以使禾苗生长,亦可以使之枯死。第二,如果此真如唯释为清净有为法,不论是正智还是无漏种现等,皆导致真如有用无体(即无真如自体相);相应只允许有“真如用熏习”,而无“真如自体相熏习”,显然违背《起信论》的原义。如前节所述,与无明互熏的真如应是如来藏,清净恒常,含藏一切如来净法,而不唯是清净有为法。综上所述,染净有为法间的增上缘关系,不能诠释真如与无明的互熏。 上述诠释的缺陷是,他们试图用一种含义去诠释熏习,没有注意《起信论》的熏习有两种含义,即同性与异性熏习。因此,问题的关键在于这两种熏习义是否矛盾。同性熏习发生在有为法间,而异性熏习讲的是有为法与无为法间的关系,二者都自成一说,正好互补,不相冲突。具体的分析可看前面第一节。下面就在此二熏习义的基础上,对《起信论》的缘起与还灭,从唯识学的角度给出一个解释。 先讨论《起信论》染法的缘起。《起信论》以真如为体、生灭为用,故在谈染法的生起时,在逻辑上必然首先解决本觉真如被覆障的问题,这就有了无明熏习真如;以此为根本前提,才有染心的生起。在前已知,真如有无为法与清净有为法两方面的含义。无明熏习真如故,真如法性被缠覆,真如所摄非阿赖耶识(无漏种)被障蔽。由此,无始以来,无明系摄如来藏,相续流转。此无始无明是染法的根本原因,即指阿赖耶识[37]。以阿赖耶识所摄杂染种子为因,生起一切虚妄分别之识,即妄心。由此妄心增上,而有妄境界之识生起。妄境界之识又返熏习妄心所摄之阿赖耶识[38],使妄心虚妄分别愈加坚固。由妄心虚妄分别,众生起惑造业,轮转生死,没于苦海。《起信论》的染法缘起义大致如此。 与此相对,根据真如与生灭的体用关系,要安立净法的缘起,得先考虑真如的作用,这就是真如熏无明,以此为内在原因,建立还灭的过程。真如自体相熏习无明,即真如(如来藏)系摄无明染法,使染法生而刹那有灭,对治可起,净法可生,乃至可有出缠成佛。但这仅是生起净法与成佛的内在根据与可能性,还需外缘助力。真如之用如来三身大用流行,随机赴感,以此为缘,配合真如自体相熏习之因,众生得以发心起行。随之,闻思修熏习真如所摄非阿赖耶识[39],闻思修下中上品辗转增上,使杂染法种子现行渐次转灭,如来净识圆满显现,亦即真如如来藏出缠。这就是《起信论》的净法生起义。四、结 语 《起信论》自南北朝末期开始流行,佛教界竞相研习,注疏浩繁,千年不衰。台贤二宗将之置于中观唯识之上,元晓法师更目之为“诸论之祖宗,群诤之评主”[40]。它是佛教天台、华严、禅宗的奠基性经典之一,进而直接或间接地影响了隋唐以后中国思想的发展。但到了上一世纪,它的思想在继续被欢呼为是对世界哲学的伟大贡献[41]的同时,在佛教界却遭到部分唯识学者的非议。批评者以唯识学为依据,力图表明《起信论》与唯识学水火不容,势不两立。而维护者亦依据唯识学去会通《起信论》,以表明二者一致。但两者不免都走入误区,批评者没有认识到瑜伽行派以唯识思想为中心,但亦有如来藏思想,二者并无矛盾,互补相成;维护者没有认识到《起信论》作为如来藏系论著,虽然与唯识学思想有涉,其思想核心却是不共的,比如真如与无明的互熏,就不满足唯识学的熏习义。本文就是在此基础上清理会通,试图阐释如来藏系思想与唯识学思想相容的一个尝试。 注 释: [18]见前注[11]。 [19]唯识学的性、相常互代,如三自相常称三自性,但此处只用其狭义,性指本性,相指相状。 [20]参考前注[5]。 [21]见前注[14]。 [22]王恩洋:《大乘起信论料简》(《大乘起信论与楞严经考辨》,张曼涛主编,大乘出版社)。 [23]守培:《起信论料简驳议》(同上书)。 [24]此中无(自)性的“性”,是本性、体之义,相是相状、本性之义。 [25]元晓:《大乘起信论别记本》p227下,《起信论疏》p217中;法藏:《大乘起信论义记》p264中;《大正藏》卷44。 [26]陈维东:《料简起信论料简》(《大乘起信论与楞严经考辨》,张曼涛主编,大乘出版社)。 [27]会觉:《起信论研究书后》;印顺:《起信平议》(同上书)。 [28]陈维东:《料简起信论料简》(同上书)。 [29]唐大圆:《起信论解惑》(同上书)。 [30]王恩洋:《大乘起信论料简》(同上书)。 [31]王恩洋:《起信论唯识释质疑》(同上书)。 [32]守培:《起信论料简驳议》(同上书)。 [33]弥勒:《瑜伽师地论》卷69。 [34]会觉:《起信论研究书后》(《大乘起信论与楞严经考辨》,张曼涛主编,大乘出版社)。 [35]唐大圆:《起信论解惑》(同上书)。 [36]陈维东:《料简起信论料简》(同上书)。 [37]根本无明是生灭依,是一切染法生起的直接原因,它可指根本无明自身,亦可指含摄它的阿赖耶识。唯识的根本依是阿赖耶识,因为它摄藏一切染净诸法的种子。从逻辑上看,阿赖耶识应为余有为法之先,故无始(根本)无明作为杂染有为法,不可能与阿赖耶识分开。这样,在会通时,可将根本无明诠释为阿赖耶识。 [38]《起信论》原文是妄境界熏习妄心,此处的妄心可指一切虚妄分别之识,但实指阿赖耶识。 [39]《起信论》原文是熏习真如,但真如还摄清净的非阿赖耶识,故此处实指熏习非阿赖耶识。 [40]元晓:《大乘起信论别记本》p226中,《大正藏》卷44。 [41]梁启超:《大乘起信论考证》(《大乘起信论与楞严经考辨》,张曼涛主编,大乘出版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