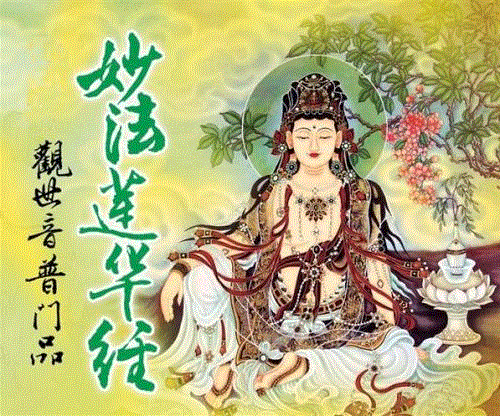论南北朝时期佛教与经学的相互渗透——焦桂美
发布时间:2024-09-03 02:49:02作者:法华经全文网佛教传入中国后,与中国传统的儒学之间经历了一个由碰撞、冲突至渐趋融合的过程。在这一过程中,二者互相影响、互相渗透,逐渐形成了互补共存之格局。但这一格局是以佛教对经学的认同与依附为前提,即二者之间的相互渗透是不平衡的,经学对佛教的影响远远超过了佛教对经学的浸染。本文仅对南北朝时期佛教与经学之间的相互渗透略作论述。
一、经学对佛教的渗透
南朝经学是从贱经尚道、通经之士盖寡的东晋玄学化经学中发展而来,经宋武帝、宋文帝、齐高帝、齐武帝及梁武帝提倡,逐渐恢复并发展;北朝虽为少数民族统治,但统治者尊经重儒,经学反较南朝发达。南北朝经学之重振凸显了经学在意识形态领域的核心地位,促进了佛徒传习、注疏儒家经典之热情,强化了佛教对儒学的依附关系,确保了儒家伦理观念的主导地位,并进一步促进了佛教的儒学化。简言之,该时期经学对佛教的渗透主要表现在以下几方面:
(一)僧徒讲习、注疏儒家经典
东晋南北朝,僧徒多兼习外书①,其根本目的是为迎合当时的主流学术思潮及统治者之好尚,以借其力量促进佛教的广泛传播,即释道安所说:“不依国主,法事难立”[1](p.32)之谓也。考察发现,东晋与南北朝高僧所习外书并不完全一样。大致说来,东晋僧侣主要涉猎《老》、《庄》,而南北朝则更热衷于儒家经典,这一演变轨迹揭示了当时的主流学术思潮即东晋玄学盛行、南北朝经学重振与僧徒学尚之间的密切关系。南北朝时期,经学的逐步恢复与发展,促进了僧侣讲习、注疏儒家经典之热情。而僧人学习儒经之因缘,情况各有不同。有出自家学渊源者,如释法通“家世衣冠,礼仪相袭”[1](p.62);有在出家前已习经者,如释慧严年12岁为诸生,博晓诗书,16岁出家又精练佛理[1](p.47);释慧约“七岁便求入学,即诵《孝经》、《论语》乃至史传,披文见意”[1](p.148),17岁始出家;也有在出家后、受僧师之命而习经书者,如释道融“十二出家,厥师爱其神采,先令外学,往村借《论语》,竟不赍归,于彼已诵,师更借本覆之,不遗一字”[1](p.42);释僧旻“七岁出家,住虎丘西山寺,为僧回弟子,从回受《五经》”[1](p.142)等等。如果说前两种情况中僧徒之经学基础主要是在出家前奠定,尚不足以反映该时期僧徒兼习外书之动机,后者则尤可注意。释道融、僧旻或受师命而习,或即随师学之,足见经学在意识形态领域的主导地位对僧徒学尚所起的引领作用。
南北朝时僧徒不但兼习儒经者众,而且有些高僧的经学修养甚至独标一时,以讲习儒家经典为时所推。如释法瑗注经、论议之隙时讲《孝经》、《丧服》[1](p.56);释僧盛特精外典,为群儒所惮,至学馆诸生常以之为胁[1](p.60)。该时期不少儒生从僧侣受经,释慧远于晋末讲《丧服》,雷次宗、宗炳等并执卷承旨[1](p.40);北朝许彦少孤贫,好读书,从沙门法睿受《易》[6](p.945)等即为明证。
僧侣阅读、研究儒家经典,有所得者乃为注疏。僧人注释儒经也因之成为该时期儒经注疏队伍中的一个特殊现象。释慧琳注《孝经》、《论语》见于《宋书·夷蛮》本传及《宋书·颜延之传》;释慧始《论语注》、释灵裕《孝经义记》、释僧略《论语解》等,均见于朱彝尊《经义考》[2]。
通过以上考察可以看出,南北朝时僧侣研习儒家经典之热情前所未有。笔者认为这一现象显然是该时期经学重振在佛教领域引起的强烈回应,而这一回应所揭示的则是僧侣对儒经的依附心理与佛教对儒学的从属地位。
(二)佛教论难以儒家经典为指导
南北朝时关于佛教问题的论难多次发生。无论双方对争论的问题及争论的结果存在多大分歧,但在立论原则上至少有一点是一致的,那就是都以儒家经典为指导,都从儒家经典中寻求立论的依据。也就是说,佛教论难如果丧失了儒家经典之凭依,佛教教义在中国也就失去了立足之地。如梁武帝时范缜著《神灭论》,不信佛教有神之说。梁武帝组织群臣答难范缜,参与者三十余人,皆表明相信佛教有神及报应等思想。为证明这些思想确实存在,他们都采取了儒佛互证的方法,广泛援引儒家经典,以证成佛教有神说之不诬。其中,通直郎庾黔娄的对答最具代表性:“《孝经》云:‘生则亲安之,祭则鬼飨之。’《乐记》云:‘明则有礼乐,幽则有鬼神。’《诗》云:‘肃雍和鸣,先祖是听。’《周官·宗伯职》云:‘乐九变,人鬼可得而礼。’《祭义》云:‘入户忾然,必有闻乎其叹息之声。’《尚书》云:‘若云三王有太子之责。’《左传》云:‘鲧神化为黄龙,伯有为妖,彭生豕见。’右七条,弟子生此百年,早闻三世,验以众经,求诸故实,神鬼之证,既布中国之书;菩提之果,又表西方之学,圣教相符,性灵无泯,致言或异,其揆惟一。”[3](p.67)可以看出,庾黔娄正是从儒家经典中寻求与佛教的共通之处,以证明佛儒“教有殊途,理还一致”[3](p.67)、“中外两圣,影响相符”[1](p.63)的观点。抛开内容之是非,单从立论原则上看,依附于儒家经典立论同样反映了经学对佛教的主导作用。
(三)佛徒认同并遵从儒家伦理
儒学在意识形态领域的核心地位决定了佛教对儒学的依附关系与从属状态,当佛教教义与儒家基本理念发生冲突时,佛教以不违背并尽量顺从儒家伦理道德为原则。早在东晋,释慧远即对佛教的出世观念与中国传统忠孝思想之间的矛盾提出了基本的处理办法,认为“佛经所明,凡有二科,一者处俗弘教,二者出家修道”,指出无论处俗弘道还是出家修道,不违背儒家忠孝观念为根本原则,所谓“内乖天属之事而不违其孝,外阙奉主之恭而不失其敬”[4](p.2392);宋世沙门慧琳著《均善论》,主张“六度与五教并行,信顺与慈悲齐立”[5](p.2391),也指出了佛教教义当以与儒家伦理并行不悖为原则;刘勰《灭惑论》云“夫孝理至极,道俗同贯,虽内外迹殊,而神用一揆。若命缀俗,因本修教于儒礼;运禀道果,固弘孝于梵业。是以咨亲出家,《法华》明其义;听而后学,《维摩》标其例”[3](p.51),亦明言孝道为道俗同贯,梵门亦须弘孝、出家当先咨亲。由以上诸例,知佛教是在认同并遵从儒家基本伦理的原则上寻求发展,即佛教在中国的存在与传播必须以遵循儒学的指导与规范为前提。违背了这一前提,佛教在中国也就失去了立足之地。从这个意义上讲,经学对佛教的渗透与制约是着眼于其基本教义与根本原则的。
二、佛教对经学的渗透
南北朝时期,佛教的深度传播使帝王、士人崇信佛教、精研佛典蔚成风气。因此风气,佛教不但浸染了通经者之思想,而且对儒家的讲经与注经也产生了直接影响。这种影响可以用广泛而深远来概括。说它广泛,是因为它的影响涉及到儒家讲经、注经的内容、语言、形式及原则等各个层面;说它深远,是因为它的某些方面(如义疏体)的影响远及此后的整个中国经学史。
(一)佛教对南北朝经学家思想之影响
南北朝皇帝、诸王及世族多与佛教结缘,对之崇信有加。上好下尚,儒佛双修或三教并重成为该时期学术风尚之主流,南北朝通经之士也因此多与佛教结下了不解之缘。南朝通经者或兼习佛典,如何胤、周弘正皆精究佛典,并有佛教著作;或与僧人交往密切,如南齐著名经学家刘瓛,虽“承马郑之后,一时学徒以为师范”,亦与僧人相往来:僧传载讲《法华》之慧基,“瓛与张融并申以师礼,崇其义训”;讲《涅槃》、《成实》之法安,“瓛与张融、何胤等并禀服文义,共为法友”。南朝经学家既精究佛典要义、又往来于名僧之间,则其思想必在一定程度上受到佛教之浸染。
北朝大儒徐遵明、李宝鼎、刘献之、孙惠蔚、卢景裕、李同轨等皆崇佛教:徐遵明、李宝鼎从僧范授《菩萨戒法》[1](p.164);刘献之曾注《涅槃经》,未就而卒[1](p.2741);孙惠蔚“正始中,侍讲禁内,夜论佛经,有惬帝旨,诏使加‘惠’,号惠蔚法师焉”[6](p.2717);卢景裕“又好释氏,通其大义。天竺胡沙门道悕,每论诸经论,辄讬景裕为之序”[6](p.1099);李同轨使梁,梁武帝“遂集名僧于其爱敬、同泰二寺,讲《涅槃大品经》,引同轨预席。兼遣其朝士并共观听。同轨论难久之,道俗咸以为善”[6](p.1241)。由以上诸例,知北朝经学家之思想亦难免佛教之影响。
南北朝时期高僧兼习外书与士子研精佛典共同构成了其时内外兼习的学术风尚,形成了当时儒佛同讲、道俗同听之盛况。如《南史·隐逸下》云马枢6岁能诵《孝经》、《论语》、《老子义》,“梁邵陵王纶为南徐州刺史,素闻其名,引为学士。纶时自讲《大品经》,令枢讲《维摩》、《老子》、《周易》,同日发题,道俗同听者二千余人。”《梁书·儒林传》云沈德威“每自学还私室讲授,道俗受业数百人”;《陈书·徐孝克传》云孝克“每日二时讲,旦讲佛经,晚讲礼传,道俗受业者数百人”;《北史·周本纪下》云周武帝“元和三年,帝御大德殿,集百僚及沙门道士等亲讲《礼记》”等等。
佛教对通经者思想之浸染,必然使佛教教义及其讲经、译经之形式、原则等在一定程度上对经学进行渗透,从而影响于该时期之经学注疏。
(二)佛教对儒经注疏内容之渗透
南北朝儒佛之间的相互渗透,使经学注疏中不可避免地杂有佛教教义。孔颖达云:“原夫《易》理难穷,虽复玄之又玄,至于垂范作则,便是有而教有,若论住内住外之空,就能就所之说,斯乃义涉于释氏,非为教于孔门也,既背其本,又违于注。”[7](p.6)又云:“熊(安生)则违背本经,多引外义,犹之楚而北行,马虽疾而去愈远矣”[7](p.1222)。由孔序推断,南北朝诸义疏援佛释经之事当复不少。因唐修《五经正义》时已多所削删,故今之《正义》涉及佛义之处几无。现存梁皇侃《论语集解义疏》(以下简称《论语义疏》)[8]所涉佛教内容并不多,主要表现为站在佛教立场上立论,将儒教称为外教或周孔之教,将佛教反视为内教等。如《先进》第十一“季路问事鬼神。子曰:未能事人,焉能事鬼”条,皇疏云“外教无三世之义。见于此句也,周孔之教。唯说现在,不明过去未来”。《述而》第七“子钓而不纲,弋不射宿”条,皇疏云:“周孔之教不得无杀,是欲因杀止杀,欲同物有杀也”。《宪问》第十四“原壤夷俟。子曰:幼而不孙弟,长而无述焉”条,皇疏云:“原壤方外之圣人,不拘礼敬;孔子方内圣人,恒以礼教为事,见壤大不敬,故历数之以训门徒也。”笔者认为,佛教对儒经注疏内容上的影响虽是显而易见的,但此类影响甚微,不会改变儒家经典的根本性质。相比之下,佛教对儒家讲经、注经的语言形式、阐释风格及阐释原则的影响更为突出,尤其值得关注。
(三)佛教对儒经注疏语言之浸染
借用佛教术语阐述儒家伦理,在当时的儒经注疏中当为常见。孔颖达《周易正义序》所列举的“若论住内住外之空,就能就所之说,斯乃义涉于释氏,非为教于孔门也”,正体现了佛教语言对儒经注疏的渗透。“住内住外”之“住”是佛教用语,指事物形成以后的相对稳定状态,“住内住外”就是指事物的本体与现象。“能”、“所”也是佛教名词,即“能知”和“所知”的简称,指认识主体和认识对象的关系[9](p.525)。今存注疏中,唯皇侃《论语义疏》中用佛教术语处尚有保留,他书因孔颖达等删削,又因现存条目盖寡,已不复见。皇侃《论语义疏》中明显有借用佛教术语之处。如《学而》第一“子曰:弟子入则孝,出则悌”条,皇疏云:“《论语》之体悉是应机适会,教体多方,随须而与不可一例责也”。此“应机适会,教体多方”即为借用佛教说法,此类词语在当时当广为僧徒所用,如释明彻云:“诸经文句既是应机所说,或有委曲深微,或复但拘名字。”[1](p.153)释僧佑在《法苑杂缘原始集目录序》中云:“夫经藏浩汗,记传纷纶。所以导达群方,开示后学,设教缘迹,焕然备悉,训俗事源,郁尔咸在。”[10](p.3374)释僧佑于《小乘迷学竺法度造异仪记序》中云:“夫至人应世,观众生根,根力不同,设教亦异。是以三乘立轨,随机而发;五时说法,应契而化,沿粗以至妙,因小以及大,阶渐殊时,教之体也。”[1](p.3374)等等。可以看出,“应机”、“随机”、“设教”等词皆与佛教有关。另外,《论语义疏序》中提出的“义文两立、理事双该,圆通之教,如或应示”的阐释原则,从字面上看“双该”与“圆通”亦借用了佛教术语。黄侃先生在其《汉唐玄学论》中指出《论语义疏》是用佛语阐释儒经的始作俑者,其说甚的:“皇氏《论语义疏》所集,多晋末旧说,自来经生持佛理以解儒书者,殆莫先于是书也。其中所用名言,多由佛籍转化,至宋人‘虚灵不至’等言语,又《义疏》之云礽已。其说圣人无梦与钓弋,皆非本事,纯由示现而为。此直刻画瞿昙、唐突洙泗矣!”[11](p.388)
(四)佛教对儒家讲经、注经形式之影响
佛教对儒家讲经、注经形式的影响主要表现在讲经时采用的设都讲、升坐、开题等形式及义疏体的注疏体式上。
1.设都讲。所谓设都讲,即讲经时选善于讲说者一人,与经师对坐于高坐之上,为之诵经书。此类讲经之法,南北朝诸史数载之。如《魏书·祖瑩传》云:“瑩年八岁,能诵《诗》、《书》;十二,为中书学生。……时中书博士张天龙讲《尚书》,选为都讲”。《北齐书·鲍季详传》云:季详“少时恒为李宝鼎都讲,后亦自有徒众,诸儒称之”。《陈书·儒林传》云:沈洙“大同中,学者多涉文史,不为章句,而洙独积思经术,吴郡朱异、会稽贺琛甚嘉之。及异、琛于士林馆讲制旨义,常使洙为都讲”。由以上记载,知南北朝儒家讲经设都讲乃常见之事。
2.升坐。

3.开题。开题亦称发题,牟润孙先生云:“盖讲经时都讲先唱题,法师讲解题意,名为开题,或曰发题”。《陈书·儒林传》云:张讥当选为士林馆学士,“简文在东宫,出士林馆,发《孝经》题,议论往复,甚见嗟赏”。《隋志》著录《周易开题义》十卷,梁蕃撰;《毛诗发题序义》一卷,梁武帝撰,当为其时开题之记录,知讲经先开题在南北朝也很流行。
牟润孙先生《论儒释两家之讲经与义疏》[12]对南北朝儒家讲经普遍采用的形式——设都讲、升坐、开题等与佛教的关系,已经做出了深入细致的研究,认为:“汉时儒家讲经求如释氏之问答辩难、升高坐、发题义者,读两汉书《儒林传》盖未之见,即三国魏晋之经师亦无之”。推断为南北朝经师仿释氏讲经之所为,其说甚确。
关于南北朝盛行的义疏体,牟先生认为亦仿自释氏,是僧徒讲经之记录或预撰之讲义,此形式为儒家所效仿。牟先生对儒家讲经、注经形式受佛教影响问题所做的探讨,深入透辟,广为征引,此不赘述。
(五)佛教对儒家讲经、注经原则之影响
值得注意的是,南北朝儒家讲经与注疏原则与两汉颇多不同:两汉注重文字训诂与章句之义,以合乎文本为阐释原则;南北朝则以释滞去惑、追求圆通为目的。笔者认为这一阐释原则的形成亦受到了佛教讲经、译经之影响。
1.释滞去惑、追求圆通与新异原则之成因
佛经要想在中国传播必须依靠翻译。魏晋以来佛经翻译虽渐趋成熟,然不尽如人意处甚多。或因中西语言习惯不同,文质、结构有异而致翻译难以切本,晋释道安故有译梵为汉有五失本[4](p.2377)之叹,鸠摩罗什亦有嚼饭与人乃令呕秽[4](p.2405)之慨;或因译者水平不一、不能兼通梵汉而致意有阻碍、传事不尽。至南北朝,佛经翻译虽日趋完善,然经中滞处仍多。因无法得见原本,僧徒讲经依赖的皆为翻译之本,受翻译水平及讲经者理解水平的限制,讲经欲逐字逐句追求经之本意,显然不太可能。这就形成了佛教译经及讲经追求通大义,能自圆其说、以通滞为上的阐释原则。释道安在《道行经序》中指出考文、寻句影响经旨的理解,提出了“率初以要终”、“忘文以全质”的讲译原则:“考文以征其理者,昏其趣者也;察句以验其义者,迷其旨者也。何则?考文则异同每为辞,寻句则触类每为旨。为辞则丧其卒成之致,为旨则忽其始拟之义矣。若率初以要其终,或忘文以全其质者,则大智玄通,居可知也。”[4](p.2372)竺道生借玄学得意忘言的理论阐明了佛经讲译不求守文、但得圆义的原则,与释道安之说实则同调:“夫象以尽意,得意则象忘,言以诠理,入理则言息,自经典东流,译人重阻,多守滞文,鲜见圆义,若忘筌取鱼,始可与言道矣。”[1](p.46)在这一原则支配下,佛教译经、讲经皆以圆通、通滞为上。后秦姚兴因旧经义多纰缪,组织鸠摩罗什等重出《大品》,“什持胡本兴执旧经,以相雠校,其新文异旧者义皆圆通,众心惬伏”[1](p.13)即说明了这一问题。南北朝时佛教的广泛传播以及佛儒兼修的学术氛围的日趋浓厚,促使佛教以圆通、通滞为上的阐释原则逐渐向儒经注疏渗透并最终成为儒家经典注疏的一般原则。
佛教讲经在圆通的前提下,还追求新异,前所举例中高僧所通之疑滞多为先旧所积,通滞即意味着除旧立新,故鸠摩罗什新译之经之所以能使“众心惬伏”,即在于“其新文异旧者义皆圆通”,释慧隆受宋明帝等敬重亦在于其能使“先旧诸义盘滞之处”昭然可了;支遁更每以“才不拔滞、理无拘新”为恨。佛教追求新异的原则同样对经学注疏产生了很大影响。
2.释滞去惑、追求圆通之原则对儒家讲经之影响
见于两《汉书·儒林传》记载的善于解滞通经的仅有两例:一为光武时之戴凭,凭习《京氏易》。《后汉书·儒林上》载光武于正旦朝贺、百僚毕会之际,令群臣能说经者更相难诘:“义有不通,辄夺其席以益通者,凭遂重坐五十余席。故京师为之语曰:‘解经不穷戴侍中’”。另为汉魏之际的谢该,该明《春秋左氏》,为当世名儒,门徒数百千人。建安中,河东人乐详条《左氏》疑滞数十事以问,该皆为通解,名为《谢氏释》,行于世。可见,两汉以来经中已有诸多疑而难决之事,被称为“疑滞”,善解疑滞谓为“通”,则“通”与“滞”盖相对而言。
时至南北朝,经中疑难之事更为突出,疏通疑滞、畅明经义成为经学发展中的一个重要课题。佛教讲经以圆通为上的原则的广泛应用也启发了儒家讲经原则的变更,从而使通滞、去惑成为南北朝讲经的共同追求。刘献之、孙灵晖、封伟伯、刁冲、徐伯珍、谢几卿、王元规等皆以善通疑滞而著名:《北史·儒林·刘献之传》云:“魏承丧乱之后,《五经》大义,虽有师说,而海内诸生,多有疑滞,咸决于献之”。《北史·儒林·刁冲传》云:冲“学通诸经,偏修郑说,阴阳、图纬、算数、天文、风气之书莫不关综,当世服其精博,刺史郭祚闻其盛名,访以疑义,冲应机解辩,无不祛其久惑”。《梁书·儒林·王元规传》云:“自梁代诸儒相传为左氏学者,皆以贾逵、服虔之义难驳杜预,凡一百八十条,元规引证通析,无复疑滞”等等。由以上诸例,知释疑祛滞、追求圆通已经成为南北朝儒家讲经的共同特点。
3.释滞去惑、追求圆通之原则在儒经注疏中的体现儒家讲经重视去惑、释滞之原则在其注疏中也得到了较好的实践。刘献之“六艺之文,虽不悉注,所标宗旨,颇异旧义”即为显例,刘氏佚文惜无遗存。从现存注疏来看,皇侃在其《论语义疏序》中较早以理论形式提出了这一原则。皇氏于《序》提出:“义文两立、理事双该,圆通之教如或应示”,又于文中数言“按文索义,全近则泥”[8](p.477),“然守文者众,达微者寡”[8](p.490),皆表达了反对拘守文字、追求“圆通”为上的阐释原则。这一原则与释道安、竺道生之论颇有相似之处。
《论语义疏》中有两个特点颇为新异:一为兼存多说,二为时出新解。如联系佛教讲经、译经原则可能对儒家注经造成的影响,《论语义疏》中的这些现象便会得到较为圆满的解释。
《论语义疏》以魏何晏《集解》为本,辅以晋江熙《集解》及他人之说,计集梁前《论语》之注近五十家,是一部汉魏迄梁《论语》注疏的集大成之作。《论语义疏》广集众家之说的注疏体例,决定了其异说并存的阐释特点。异说并存之例在《论语义疏》中较为普遍,如《子张》第十九“曾子曰:‘堂堂乎张也,难与并为仁矣’”,郑注:“言子张容仪盛而于仁道薄也”。皇疏:“言子张虽容貌堂堂而仁行浅薄,故云难并为仁。江熙曰:‘堂堂,德宇广也,仁行之极也。难与并仁,荫人上也。’然江熙之意是子张胜于人,故难与并也”。此条皇疏先申郑注,又引江熙说,郑以“堂堂”指容貌,江指德行,从而致二说歧义。《颜渊》第十二“子曰:片言可以折狱者,其由也与”,皇疏:“夫判辨狱讼必须二家对辞,子路既能果断,故偏听一辞而能折狱也。一云子路性直,情无所隐者,若听子路之辞亦则一辞亦足也”。皇疏二义,前为子路听讼者一方之辞即能折狱,后者则谓听子路一人之辞即可断狱,此条因“片言”无主语而致歧义。可以看出,皇侃对此类异说往往客观保存,不加评论。笔者认为,皇侃疏解诸家、兼存众说的最根本的指导原则便是以圆通为上,即在圆通的基础上寻求对诸家之说的选择、取舍与整合,以最终体现皇侃个人的阐释思想与阐释理念。
除了以上异说并存之例外,《论语义疏》中还有一些颇为新异的阐释。如《公冶长》第五“宰予昼寝”条,皇疏引释慧琳说,云:“宰予见时后学之徒将有懈废之心生,故假昼寝以发夫子切磋之教,所谓互相影响者也”。《阳货》第十七“宰我问三年丧期”条,皇疏引缪播说,云:“尔时礼坏乐崩,而三年不行,宰我大惧,其往以为圣人无微旨以戒将来,故假时人之谓咎愤于夫子,义在屈己以明道也”。这两条中宰我昼寝及问三年之丧本来显示的是宰我个人的真实思想,慧琳与缪播却将其阐释为宰我有意为之,目的在启发圣教、救助时弊,说固新巧而有思致,却远离了文本原意。此类阐释在《论语义疏》中尚多,当有其产生的深层原因。撇开其中的原因不谈,以上两例是南北朝经学追求新异的阐释原则在注疏中的切实实践。
综上所述,笔者认为,南北朝时期儒家讲经与注疏中释滞去惑、讲求圆通、追求新异的阐释原则的形成虽导源于两汉,然归根到底,以受佛教讲经、译经的影响尤大。
三、佛教与经学相互渗透的不平衡
南北朝儒佛二教虽互有渗透,但这种渗透是不平衡的,其不平衡性大约可以从两个层面来认识。
(一)佛教无条件地受着经学的制约与规范
由以上论述可以看出,佛教必须依附于儒学而存在,失去了这一基础,佛教也就不可能立足于中国。因此,佛教必须遵循儒学的基本精神,并以此为基础对佛教自身进行改造,从而促进佛教的中国化,而佛教中国化的实质归根到底是佛教的儒学化。换言之,经学对佛教起着制约与规范作用,佛教必须无条件地接受这种制约与规范。
(二)经学有选择地从佛教中汲取有益成分
与佛教无条件地接受经学的制约与规范不同,儒学对佛教的接纳与吸收是自由的、有选择的。我们看到,虽然南北朝经学家多结缘于佛教,但佛教对儒家讲经、注经的影响主要表现在形式上的借鉴而非教义上的渗透。这正如刘宋颜延之对释慧琳的态度。颜延之本人亦信佛且曾与慧琳同为彭城王义真所宠,当有志趣相投之处。但当慧琳以文学为宋文帝赏爱,召见常升独榻时,延之以“同子参乘,袁丝变色”[5](p.1902)相谏,是拒僧徒于政权之外也。也就是说,儒学对佛教的认纳同样是以不违背儒家思想为原则的。想以释家戒律来改革儒家礼制仪文,即使挟帝王之重也是行不通的。梁武帝于天监年间曾一度制定庙祭、郊天不得杀牲,代以采蔬的制度。然而,这一改革梁武身殁即废正说明了儒家礼制的不可动摇并进一步折射出儒佛二家的主从关系。刘晓东先生指出,南北朝时期“释道对于礼教的作用,只形成了一种对立性的互补,而不是侵蚀性的染变”②,笔者认为这种作用实际上适应于该时期儒学与佛教的全部关系。
注释:
①僧徒把佛经之外的书称之为“外书”。
②刘晓东先生云:“从释、道宗教对礼教的影响看,两晋的道家代表人物葛洪就精研《丧服》,著有《丧服变除》一卷。刘宋时期释慧远讲授《丧服》,儒生雷次宗、宗炳都去听讲。又释法瑗也是‘论议之隙,时谈《孝经》《丧服》’。萧梁何胤既精信佛法,又继王俭、张绪而修撰新礼。可见当时儒生谈佛、僧人论礼,两不相妨,蔚成风气。至于像梁武帝既大倡礼学,又精信佛法,天监年间曾一度制定庙祭、郊天不得杀牲,代以采蔬。然而这一改革梁武身殁即废。可见梁武虽挟帝王之重,欲以释家戒律来改革礼制仪文,也是行不通的。”《论六朝时期的礼学研究及其历史意义》,《文史哲》,1998年第2期。
【参考文献】
[1]梁·释慧皎,等.高僧传合集[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影印宋碛砂版《大藏经》本,1995.
[2]清·朱彝尊.经义考[M].北京:中华书局影印《四部备要》本,1998.
[3]梁·释僧祐.弘明集十[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影印宋碛砂版《大藏经》本,1994.
[4]清·严可均.全晋文[M].北京:中华书局影印清光绪年间黄岗王毓藻刻本,1999.
[5]梁·沈约.宋书[M].北京:中华书局排印校点本.
[6]唐·李延寿等.北史[M].北京:中华书局排印校点本.
[7]唐·孔颖达.十三经注疏[M].北京:中华书局影印世界书局本,1979.
[8]梁·皇侃.论语集解义疏[M].台湾:台湾商务印书馆影印《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9]张岂之.中国思想史[M].西安:西北大学出版社,1989.
[10]清·严可均.全梁文[M].北京:中华书局影印清光绪年间黄岗王毓藻刻本,1999.
[11]黄侃.中国现代学术经典·侃卷·汉唐玄学论[M].石家庄:河北教育出版社,1996.
[12]牟润孙.注史斋丛稿·论儒释两家之讲经与义疏[M].北京:中华书局,198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