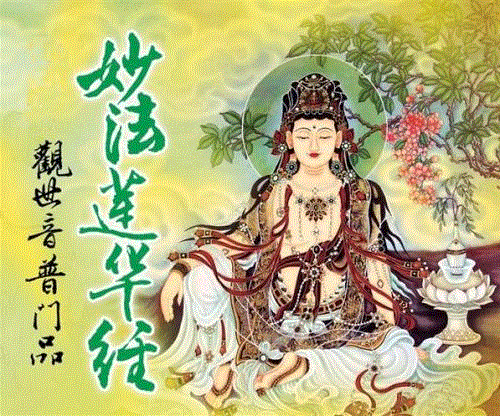“典型在夙昔”?
发布时间:2022-04-15 21:09:45作者:法华经全文网“典型在夙昔”?
释昭慧

十月九日起,笔者在中国大陆展开了一趟为期十二天的“学术之旅”——在天津“弘一大师圆寂六十周年学术研讨会”上发表论文;拜会上海复旦大学宗教研究所所长王雷泉教授,北京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宗教研究所副所长张新鹰教授、社科院佛教研究室前主任杨曾文教授、现任主任方广錩教授、副主任魏道儒教授,中国人民大学佛教与宗教学理论研究所张风雷与宣方教授,并蒙是诸学界前辈或同道之邀,在上述三个学术单位做了四场学术性的演讲,讲题有理论层面的,也有实务层面的,涵盖了佛学研究法、伦理学、戒律学、台湾佛教女性运动与台湾佛教现况等范畴。
这次虽是学术之旅,基于佛弟子“不忍圣教衰”的心肠,最关切的其实还是大陆佛教的发展情形。尽管所见可能过于片面,不足以论断全局,但还是要以宗教人的情操与知识份子的良知,真诚地将所见所感,向读者分享如下:
简绘佛教学者群像
在大陆拜见的几位学界前辈与同道,笔者此下依先后顺序,粗略描绘一下对他们的印象:王雷泉教授坦率直言,而且对佛教有一种“老臣谋国”的忠诚;他深知“中兴以人才为本”,所以虽然教务繁重,他仍仆仆风尘地往来于内地各佛学院,向僧众教授天台学与宗教学。从他与笔者闲谈之中,所表达对某位大陆知名文学家“风骨不足”的评价,也可看出他以一介“独立学者”,对社会现况持有一种敏锐而犀利的批判精神。
张新鹰教授含蓄内敛,对佛教保持一种作为学界人士所应有的,谨慎而礼貌的态度,但这不代表他对佛教界没有一份深厚的关切;犹记得笔者在社科院的演讲题目是“佛教界的女性运动——理论依据、行动策略与运动实效”,他听完了具有如此强烈批判意识的演讲之后,不但不以为忤,反而语重心长地说:“今日的台湾佛教,或许就是明日的大陆佛教。”事后并来函告知笔者:“佛教作?中国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是我们在现代化进程中必须重视和善用的宝贵精神资源,这就是我们何以如此关心其现状及发展并愿意倾听台湾佛教界、学术界有关见解的主要原因。”
同一研究单位中的老前辈杨曾文教授,有一种古之儒者温柔敦厚的气质,但基于学术良知,再加上山东人爽直的性格,还是会表达一些自己对佛教界的观察与评议。他对台湾的“废除八敬法运动”,就曾于五月六日莅临佛教弘誓学院公开演说之时表示:学界人士不便介入教界行事,但有“下判断”的能力。他并公开撰文,对笔者的“佛门两性平等”运动给予极高评价,并认为大势已因此形成,不可能再逆转过来。这给了笔者极大的精神鼓舞!
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宣方教授,可能因为年纪较轻,在生命中没有经历过文革的阴影,所以热情耿介,对佛教现况,更是直言无讳。据他告知:在漳州有一场佛教界所举办的学术研讨会,他“哪壶不开提哪壶”,竟于会上力陈“废除八敬法”之意义。他叙述此事时,对自己所碰到的无礼待遇,显然也不以为忤。我笑言:“世道人心就是如此!”在台湾,又何尝没有少数比丘尼忙着与笔者的女性运动划清界线,并向大男人比丘表态输诚呢?
知识份子的忧患意识
总的来说,这些学者让我感佩的是:他们显然有一种作为中国知识份子强烈的忧患意识,无论是对于他们所研究的中国佛教,还是对于他们所置身其中的中国社会,都有高度的关切与爱护之情。特别是:中国社会无论是在政经局面或在思想文化方面,都已面临剧烈的变动,相对于此,中国佛教的内部,似乎还极少人意会到:他们站在这个历史的转捩点上,应该做些什么明确的思想改革或制度改革,期以复兴教运?这让护念佛教的学者不能不产生某种程度的焦虑感!但是,由于过往特殊的政治背景中,学界人士对佛教曾发出些不友善也不公允的言论,所以至今佛教界倘遇到学界的批评,还是难免会有强烈的“被迫害意识”;而学者们带着前人犯错的“原罪意识”,即便是想发出一些善意的批判,话到口边也只得礼貌地强忍下来。
然而,当局者迷,旁观者清,一群有宏观世局之眼光的学者,假使客气地噤声了,长远来看,这会是对佛教有利的局面吗?僧侣们怕被学者诤言“刺痛”的心理是可以理解的,但是自来忠言难免逆耳,在每一人或每一团体自我修正以成长的过程之中,谁不须要“察纳雅言”以付出“被刺痛”的代价?怕痛,恐怕不是什么好事!
退一步言,即便有些学者的批评是不公道、不如实的,佛教又何妨抱持“有则改之,无则嘉勉”的心胸来看待它们?即便是针对不实言论而加以反驳,也好过端出“僧事僧决”的帽子,或是谴责“白衣上座”,以十足的阶级意识,拿来杜人悠悠之口。即便他们竟把学界诤言,一概当作是敌意之论,也要谨记住“无敌国外患者,国恒亡”的古训!太过安逸而又欠缺监督的环境,对佛教长远的前途来说,实在不是什么好事!
一切归咎宗教法令?
记得十月十九日在人民大学的那场演讲之中,宣方教授回应笔者的演讲时,问到笔者本次大陆之行,于所见所闻之中,对中国佛教的看法。笔者基于爱深责切之情,乃不敢隐讳,直抒所见的“片段观感”云:
我昨晚在北京搭计程车时,司机先生的一席话让我感触良深!他说:“我真想参加天主教的弥撒,听听神父们讲道。到寺庙里,进门要买门票,进来之后,给你几只香,上香之后,叫你丢二十块进功德箱,也看不见有谁给我们讲讲道理,这有什么意思?”这是社会底层人民心声的一小部分缩影,佛教中人似应重视。
也许这种爱深责切之论,实在是太过直接而毫不修饰,不小心刺到了少数爱教人士的自尊心,当场立刻有人反驳笔者:你不瞭解中国佛教,中国佛教事实上是受限于宗教法令,无法像台湾佛教一般挥洒自如。
笔者当即反问:即便是受限于宗教法令,但请问:在宗教法令所容许的范围之内,佛教又尽到了全部心力吗?是的,宗教法令不容许在宗教场所以外的地方传教,但是在它所容许的寺院范围之内,为什么会出现那位司机先生这般的怨言呢?
其次,研究宗教的人都知道:历来宗教倘真遇到政治迫害,只有更加团结,更加壮大,但佛教呢?中国过往的宗教政策容有过失,但如今对佛教大体来说还没构成“迫害”,而且颇有善意扶持的倾向,请问:我们还能把教运不振的责任,都一股脑儿怪罪于政治力的干预吗?
再者,宗教政策容或有所不当,那么,佛教界正应努力争取其改善空间。要知道:权利是要靠自己争取来的,不会是从天上自动掉下来的。
发言者反驳笔者云:“这会有危险!这样不安全!”
笔者至此忍不住略带嘲弄地反问道:“是吗?你们在意的就是不危险而很安全?如果人人如此,那就不要怪罪宗教政策了。”
佛教的慧根何在?
也有人以“衣冠上国面对边陲之邦”的高姿态告诉笔者:“未来佛教的慧根一定是在中国而不是在台湾。”
笔者心平气和地答覆他:“我是以‘无私无我\’的心态来到此地面对大家的。即使是对台湾佛教的负面现象,我也直言不讳。‘革命不是请客吃饭\’,复兴佛教的艰钜工程,就更不是请客吃饭,讲些应酬的门面话,是没什么意思的!我对大陆佛教的观察,容或片面而不够周全,但我的善意则请万勿怀疑!即便大陆佛教与台湾佛教有些差异与矛盾,但那也应属‘人民内部的矛盾\’,而非‘敌我的矛盾\’,你毋需用如此防卫的态度来回应我。
“我十分乐意见到大陆佛教比台湾佛教更为强大而兴盛,这不但是佛教之福,也是众生之福!但是我希望你不要用‘宿命论\’的方式,作些毫无理据的预言,那是不符合‘缘起论\’的。我衷心希望你的预言成真!但未来佛教的慧根在不在中国大陆,这要看你们的努力,而不能徒托空言!而且,时不我予!司机先生的话,犹如一记警钟!我不希望看到那么一天,中国大陆已有十亿人口选择了放弃佛教,届时,你的‘未来佛教的慧根一定是在中国\’之论,要等着应验也来不及了!”
宗教当局的善意态度
笔者是一个“佛教主体性意识”非常强烈的佛弟子,一向对佛教中人“抱住特定政党大腿”而锦上添花的作风,都表达着笔者锐利的批判态度。直至如今,对于任何政党,只要他们对佛教有不友善之举措,或是其政策有损于社会良善风俗或弱势众生,笔者一概是笔下毫不留情的。对台湾政治所抱持的态度尚且如此,更何况是对那“天高皇帝远”而“管”不到笔者的共产政权呢?
但是,容笔者说一句中国佛教僧伽可能会甚觉“刺耳”的话,在笔者所接触过的中国大陆宗教当局官员之中,已有越来越多人对佛教发出了强大的善意,并且近期还透过基层培训的方式,让地方基层的宗教官员,改变他们过往对宗教的倨傲态度,强调要正面地“帮助宗教解决困难”。
即便是站在“政权利益”的角度以考量宗教,他们也已知道:行事正当而非暴力主义的宗教,对于社会秩序的稳定,良善风俗的维系,苦难同胞的救护,都是具足稳定性力量的。此所以一些宗教官员,即使身为佛教的“局外人”,对于佛教也难免会有一种“恨铁不成钢”的心情。
以本次的天津之行为例,笔者参加的纪念弘一大师研讨会,是由民间团体李叔同研究会主办,并由官方的河北区文化局协办的,所以笔者此行非常低调,并没有告知任何宗教当局的官员。但是不料天津市宗教局副局长孙凤年先生闻知笔者来到,不但主动安排了李仁智局长与他个人对笔者的一场邀宴,更重要的是,他还在天津大悲院安排了一场长达三个小时的座谈会,邀请天津市佛教会的领袖宝函长老、王剑非与李可家居士等,以及年轻有为的比丘智如、演龙二位法师、李莉娟居士(弘一大师孙女)到场,并请笔者谈谈台湾佛教的发展状况。他不讳言自己于年初参加佛指舍利恭迎团,来到台湾之时,看到了台湾佛教的盛况,颇有感触,很希望天津佛教界能够以现有良好的资源而开创新局。
也告知笔者,对于园林旅游局管理寺院,纯粹当作观光胜地,他是不以为然的。他正积极争取盘山几座寺院的归属权,希望它们能改由宗教局管辖,而让僧人入驻寺中,展开教化工作。即使像孙局长这样爱护佛教的宗教官员,不能代表所有省份宗教官员的共同态度,但这无论如何总也算是官方对佛教界的一部分“缩影”吧!
献身甘作万矢的
天津李叔同研究会会长李载道先生并不是佛教中人,甚至有着浓厚的“官方色彩”,但他更有文化人的气质。早在他还担任河北区党委书记期间,就极力促成弘一大师故居与梁启超居士故居的修复。前人艰难种树,如今树已成荫。本次梁启超故居(包括他的书斋“饮冰室”)开放前夕,我们得以在文化局安排之下先行参观了这两座古雅楼房,及其中所陈列的梁先生相关文物;明年此时,弘一大师故居亦将修复竣工而开放参观。为了修复梁先生故居,官方拆迁了九十一家住户,耗资两千万人民币。显见他们对于乡梓之中出现了“国之典范”,有着一种“与有荣焉”的深厚感情。
这是一个缺乏“典范”的时代,只要有“典范”存焉,人们还是会油然生起“心向往之”的深情!对“献身甘作万矢的,着论求为百世师”的梁启超先生是如此,对那沉吟“亭亭菊一枝,高标矗劲节,云何色殷红?殉教应流血”的弘一大师,又何尝不是如此?
但是,在“风檐展书读”而孺慕古昔典范之际,这些教外朋友们,难道不会浩然太息:果真是“哲人日已远”,典型尽“在夙昔”吗?
站在梁启超英姿飒爽的铜像之前,笔者不胜欷歔!早在民国初年,他已凛然发出“人权与女权”的谠论;时至今日,中国社会已一步步迈向男女平权之理想,不意中国佛教竟然还将男尊女卑,赋与“圣教量”的正当性,悍然抗拒着改革的力量,无视于社会的鄙夷。倘梁先生活在今日,肯定要为同样“献身甘作万矢的”的后生小子之笔者,助上一臂之力吧!
九十一年十月二十四日,于尊悔楼
——摘要版刊于九十一年十月二十六日《自由时报》“自由广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