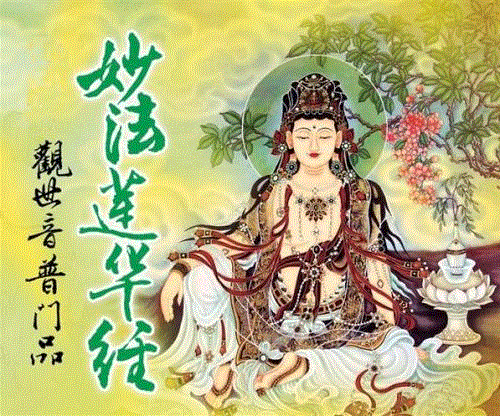“沩山田”与“沩山牛”——对沩仰宗的省思
发布时间:2022-03-05 10:19:34作者:法华经全文网今年九月底,湖南宁乡举办了“中国禅?沩仰论坛”,笔者在会上作了题为《“沩山田”与“沩山牛”》的即席发言,获得与会的赞好。回来后,因赶著完成《虎丘禅系概述》一书,因而也就无暇去检故了。今此书初步定稿,因将昔日发言的要点拈出,其中似仍有可资借鉴者,因而将之连缀成文,以俟方家郢政。
一、“沩山田”──对农禅的省思
在中国佛教中,农作引入其中,似乎并不起源于中唐时期的百丈怀海,在早期佛教的弘传中便已出现了。据佛门中的文字记载,最早的引农作到教中者恐怕要数刘宋时期的译经大师昙摩密多了。据慧皎《高僧传》卷三所载,昙摩密多“到炖煌,于闲旷之地建立精舍,植奈千株,开园百亩,房阁池沼,极为严净” [一]。与昙摩密多几乎同时代的道安大师早年也曾“驱役田舍”,从事农作;稍后的西行求法大师法显曾经“与同学数十人于田中刈稻”,并以佛法开示夺谷的贼人;而在北方的长安,僧人的种麦于寺院中,已经见于《魏书?释老志》了。至四祖创立双峰道场,则农作已经纳入了禅僧的日常生活之中;迄乎五祖在黄梅开东山法门,农作则更是僧家的常课了。《楞伽师资记》载弘忍大师居双峰山幽居寺时,他“缄口于是非之场,融心于色空之境,役力以申供养,法侣资其足焉”[二]。由此可见,弘忍时期的禅宗道场虽然推行农作,但并未像后世那样把禅修纳入农作之中,使二者形成一个浑然的整体。
到了开一代农禅风气的百丈那里,虽然有“一日不作,一日不食”的美谈在寰宇传播,但在百丈《语录》中,除了“闻鼓声,归吃饭”[三]的那则公案外,所载他的农禅的事迹似乎并不太多。幽居南泉修持的普愿禅师,尽管他亲自参加农作,著名的“刈茅”公案[四]便是其例,然其《语录》所载农禅的机缘亦不多。
真正把农禅作风掀向高潮的应当算沩仰灵祐师徒。在今日宁乡县的密印禅寺周边,有不少被称为“罗汉田”的小型农田,相传就是唐代的灵祐师徒之所开创。且当初百丈道场的规模也仅仅达常住八百众的规模,而在沩山则是容纳千五百善知识的大道场,要解决这多僧众的日食,坚持农禅作风的实际意义也就更为凸显出来了。由此,把农作切实地纳入具体的禅修之中,已经成为了沩山道场的重要举措。综观所有禅门文献,可以说没有哪位禅师的语录中记载农禅事迹有沩山之多的,这就足以见出农禅在沩山道场中的重要地位了。我们且来看看沩山师徒采茶的那则公案:
师摘茶次,谓仰山云:“终日摘茶,只闻子声,不见子形。”仰山撼茶树。师云:“子只得其用,不得其体。”仰山云:“未审和尚如何?”师良久,仰山云:“和尚只得其体,不得其用。”师云:“放子三十棒。”仰山云:“和尚棒某甲吃,某甲棒阿谁吃?”师云:“放子三十棒。”[五]

在沩山与仰山师徒这里,他们通过采茶的劳作,把对禅法的“体”、“用”的领会贯彻进来了,因而也使得这寻常的劳作变得活脱起来了。在他们师徒这里,农作不仅是解决僧供的重要途径,同时更是参学解脱的殊胜道场。事实上,也只有在这种意义上,才称得上是真正的农禅:农作因禅修而注入了活力,禅修因农作而获得了生活保障。像这样的例子,在沩山师徒的勘辩机缘中还很多,再举几例如次。
?师问仰山:“何处来?”仰山云:“田中来。”师云:“禾好刈也未?”仰山作刈禾势。师云:“汝适来作青见,作黄见,作不青不黄见?”仰山云:“和尚背后是甚?”师云:“子还见?”仰山拈禾穗云:“和尚何曾问这个?”师云:“此是鹅王择乳。”[六]
?沩山一日指田问师(仰山):“这丘田那头高,这头低。”师云:“却是这头高,那头低。”沩山云:“尔若不信,向中间立看两头。”师云:“不必中间立,亦莫住两头。”沩山云:“若如是著水看,水能平物。”师云:“水亦无定,但高处高平,低处低平。”沩山便休。[七]
?合酱次,师(沩山)问仰山:“这个用多少盐水?”仰山云:“某甲不会,不欲祗对。”师云:“却是老僧会。”仰山云:“不知用多少盐水?”师云:“汝既不会,我亦不答。”晚间,师却问仰山:“今日因缘,子作生主持?”仰山云:“待问即答。”师云:“现问次。”仰山云:“耳背眼昏,见闻不晓。”师云:“凡有问答,出子此语不得。”仰山礼谢。师云:“寂子今日忘前失后,不是小小。”[八]
?仰山蹋衣次,提起问师(沩山)云:“正恁时,和尚作生?”师云:“正恁时,我这里无作生。”仰山云:“和尚有身而无用。”师良久,却拈起问云:“汝正恁时作生?”仰山云:“正恁时,和尚还见伊否?”师云:“汝有用而无身。”师后忽问仰山:“汝春间有话未圆,今试道看。”仰山云:“正恁时,切忌勃诉。”师云:“停囚长智。”[九]
在以上四例中,第一例是以“刈禾”的农作展开机辩的。在收割稻谷的同时,沩山师徒就稻穗的青、黄、不青不黄来进行机辩,从而超越世法的有、无、非有非无等一切边见,进入佛家的中道实相义之中。值得注意的仰山最后的拈起稻穗问沩山“和尚何曾问这个”,获得了灵祐“鹅王择乳”[一○]的赞赏,乃是因为仰山能够就具体的稻穗当体透过一切边见,直超圣域。第二例是平整水田的公案,这也是江南农田作务中的必要工序。沩山首先以“这丘田那头高这头低”来激发起仰山的疑情,而仰山也当下知机,他反而以“却是这头高那头低”来应对。但沩山仍不放过仰山,他要求“向中间立看两头”,而仰山则对机迅疾,他的“不必中间立,亦莫住两头”一语,便扫荡尽了一切边见。事实上,所谓高低之见,无非是来自于人们寻常的执著,若站在平等一如的禅观上来观照,自然是没有高低的。然在最后,沩山还要求以农田平整的通常做法,要求放水到田里来看是否平整,而仰山却指出“水亦无定,但高处高平,低处低平”。好一个“水亦无定”,它把世间一切事物“无自性”的特性表述得非常透彻。由此也可以看出,沩仰禅在平和的接机中,不但要使学人达到“离四句,绝百非”的境地,最后乃至连同这一殊胜境界也得扫荡干净。第三例是在“合酱”的食品加工作务中展开,沩山以“这个用多少盐水”问仰山,从而开始他们师徒的机辩。仰山当下知机,便以“某甲不会”来促使沩山答话。而沩山虽然说过“却是老僧会”,但面对仰山的具体提问,同样以“汝既不会,我亦不答”来接引。就这样,他们师徒将这一机缘上暂时悬置了起来。到了晚上,沩山再度叩启仰山“今日因缘,子作生主持”,而仰山则以“耳背眼昏,见闻不晓”来应对。最终当仰山礼谢沩山的“凡有问答,出子此语不得”时,得到的是沩山“寂子今日忘前失后,不是小小”的忠告,可见沩仰禅在体用上是要求穷源彻底。第四例机辩是在“蹋衣”的作务中展开,沩仰师徒就衣服与穿衣的人(“体”与“用”)之间进行勘辩。其中仰山的“和尚有身而无用”,暗示了沩山在此时注重禅法之“体”而忽视其“用”;而沩山反驳仰山的“汝有用而无身”,无疑也暗示著仰山得“用”昧“体”的缺失。自然,作为沩仰禅的最圆满境界,非但要超越一切有无对待,而且还要达到体用圆融的境地,至此方能罢手。
其实,在沩仰师徒的寻常问讯之中,也无不就农作等事宜展开禅机,下面的这则公案便是其例。
夏末问讯沩山次,沩山云:“子一夏不见上来,在下面作何所务?”师云:“某甲在下面锄得一片畬,下得一箩种。”沩山云:“子今夏不虚过。”师却问:“未审和尚一夏之中作何所务?”沩山云:“日中一食,夜后一寝。”师云:“和尚今夏亦不虚过。”道了久吐舌。[一一]
在解夏之后,仰山去看望沩山,在尽师徒之礼后,沩山便问他一夏在山下干些什,而仰山的回答是“某甲在下面锄得一片畬,下得一箩种”。而当仰山问沩山一夏是如何过的时,沩山告诉他“日中一食,夜后一寝”,而师徒两人的评价同样是“今夏不虚过”。如果略加审细,则不难发现在仰山的开荒与下种农作之中,寓含了开垦心田的荒地、播种菩提种子的深意;而沩山的“日中一食,夜后一寝”,自然也具有大珠慧海“吃饭睡觉”[一二]之机锋。假如我们把沩仰师徒很平常的寒暄当作等闲看待,则会错会其中喷薄而出的禅机,也会错会沩仰禅的真实意趣。诚然,如果要按照印度佛教的结夏制度,在这一时期内僧人是应该禁足的,更何况是开荒播种这些农作可能伤害地下虫子的事情?而佛教在传入中国的过程中,对于农作便从未废止过,更何况禅宗已将印度佛教彻底中国化了。
在沩山门下,其门人的开悟因缘也有不少与农作直接相关的。例如香严智闲禅师,他早年在百丈门下时,能做到“问一答十,问十答百”。后来,百丈圆寂了,香严依止在沩山门下,沩山于是要他在“父母未生时试道一句看”。谁知沩山的这一问,却使他翻阅平昔所看过的一切经教文字也答不上来,而他屡屡乞求沩山给他说破,可沩山就是不说。他最后只得把平昔所看的文字统统烧掉,“且作个长行粥饭僧,免役心神”了。也就在他经过沩山激发而游方之后,香严在忠国师遗迹上栖止,一天因芟除草木,偶尔将一块瓦砾抛去,不料却击中了土地外面的翠竹,发出清脆的响声。而恰好是这击脆响叩启了香严的悟缘,终于使他明白了沩山“父母未生前的一句”,他因此沐浴焚香,遥礼沩山说:“和尚大慈,恩逾父母,当时若为我说破,何有今日之事?”[一三]像这样生动的悟道因缘,何尝又不展示了沩仰宗风中的农禅特色呢!
其实,沩山不但将禅教贯彻在日常的农作之中,他本人也身体力行,经常从事各种农作。例如,有次,地方官吏李军容来沩山,灵祐正在泥壁(粉墙),李只好在沩山背后庄重地持笏站著。灵祐尽管回头看见他来了,但并没有放下手头的活计,而是以“侧泥盘作接泥势”来接引李氏。而李军容也当下知机,他把笏板转过去,作出接泥的样子。此时,沩山才放下手头的泥盘,带领李一道进方丈去。[一四]
如此多的农禅例子,除了《沩山语录》以外,其他禅师的机缘语录中是很难见到的,可见,农禅在沩山已经成为了禅僧的一种自觉的禅修活动。在农作中贯注了禅修的内容,则使农作不只是作为一种简单的劳动出现,也不只是成为解决僧供的一种需要,而是作为人生解脱的一种修行。反之,引禅修入农,同样可以解决僧人的日食所需,这样可以使僧人生活必需品由依赖檀越的布施转换到自给自足之中。这种寺院经济形式避免了僧人对社会、特别是对统治者的依赖性,强化了僧人修学的主体自觉意识,则自然也可以使佛教走向更为独立自主的道路。
二、“沩山牛”──对沩山禅次第的省思
站在禅的修行阶次上讲,沩山禅认为有悟道、见道、护持、水牯牛(乘愿再来度生)这样四个阶次。关于修禅见道后的护持,在诸多禅师咐嘱其见道弟子时,往往有“珍重”、“善自护持”等语,而在沩山,也不例外。灵祐在一次上堂时说:
夫道人之心,质直无伪,无背无面,无诈妄心,一切时中,视听寻常,更无委曲,亦不闭眼塞耳,但情不附物即得。从上诸圣,只说浊边过患,若无如许多恶觉情见想习之事,譬如秋水澄渟,清净无为,澹泞无碍。唤他作道人,亦名无事人。……若真悟得本,他自知时,修与不修是两头语。如今初心,虽从缘得,一念顿悟自理,犹有无始旷劫习气未能顿净,须教渠净除现业流识,即是修也。不可别有法教渠修行趣向,从闻入理,闻理深妙,自心圆明,不居惑地。纵有百千妙义,抑扬当时,此乃得坐披衣自解作活计始得。以要言之,则实际理地,不受一尘;万行门中,不舍一法。若也单刀直入,则凡圣情尽,体露真常,理事不二,即如如佛。[一五]
在这里,沩山老人认为:道心应是“质直无伪”的,必须使自心如秋水澄渟,方可称作道心,或名为“无事人”(按:丹霞天然禅师也曾以“无事僧”自称)。这就是要求学人断除一切人我法执,做到“情不附物”,方可证得此心,做个无事的人,这便是大师劝化学人悟道修行的法门。其实,大师开示学人所悟得之道,也就是大师所要求证得的那颗“初心”。所谓“初心”,便是学人那颗本来就具备了且未被污染的清净心,它是一切有情本自具足的如来清净藏识。学人经过一番刻苦的修持后,一朝真心显露,即便识得了初心,也便见到了自性,这就实现了禅家所说的开悟。
然而,禅僧的开悟见道,并不见得就达到了修行的终极点。因此,沩山老人认为:“如今初心虽从缘得,一念顿悟自理,犹有无始旷劫习气未能顿净,须教渠净除现业流识,即是修也。”这也就是说:禅者悟道后,仍须有一个“护持”的阶段,方可使其已悟之禅境不至于退转,方可尽除其无始劫以来的无明业障。这一主张,在当时的丛林中已实施了,且各大禅师在咐嘱其见性之徒时,均语重心长地向他们道声“珍重”或“善自护持”。可见,禅者悟道后,若弃渐修,便会退转,乃至堕落。因而,沩山在开示学人中,明确地指出了参禅道人在悟后必须坚持再修行,这便为禅门明确地指出了一个修行的阶次。在《沩山语录》中,还载有这样一桩公案:
灵云(志勤禅师)初在沩山,因见桃花悟道,有偈云:“三十年来寻剑客,几回落叶又抽枝。自从一见桃华后,直至如今更不疑。”师(沩山)览偈,诘其所悟,与之符契。师云:“从缘悟达,永无退失,善自护持。”[一六]
沩山在这里对志勤禅师的咐嘱,正如当年乃师百丈对他所咐嘱的“汝今既尔,善自护持”如出一辙。这则公案,有力地说明了禅者见道之后,还必须有一个善自护持,长养圣胎的修习过程。因为一时的见道,绝不意味著终生大事就完结了,不用再修了。
其实,当年沩山的同参长庆大安在修学于百丈时,也经百丈开示了禅修的这一阶次。
师(大安)即造百丈,礼而问曰:“学人欲求识佛,何者即是?”丈曰:“大似骑牛觅牛。”师曰:“识得后何如?”丈曰:“如人骑牛至家。”师曰:“未审始终如何保任?”丈曰:“如牧牛人执杖视之,不令犯人苗稼。”师自兹领旨,更不驰求。[一七]
在这里,“觅牛──骑牛──牧牛”这三个阶次,分别譬喻悟道、见道、护持这三个修持阶段。沩山所开示学人的修持阶段,与乃师如出一辙,这便足可见出禅门的“养子方知父慈”来。值得注意的是,从百丈的此次开示之后,以“牛”为喻的说教便在丛林中盛传开去,例如南泉的“向异类中行”,沩山的“水牯牛”,至宋廓庵禅师还作有“牧牛图”。若穷其源,恐怕还得首称百丈老人。
由悟道而见道的禅师,在禅门文献记载中可谓俯拾皆是了,何况尚有一些已得道或已悟道而未了的禅师未载诸禅史。从史书记载来看,仅唐武宗会昌毁佛一事,天下所拆寺院就达四六○○余所,澄汰僧尼达二六○五○○人之多[一八]。由古至今,如许多的出家释子,当他们剃发染衣之时,何尝不曾发过大心呢!然而,沙门之中果真见道乃至证得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者,毕竟为数不多,这便是一个十分值得思考的问题。可见,悟道、见道、护持这三个修持环节,是丛林中所不容忽视的,否则,学人或将不见道,或者虽见道而不得正果。从丛林修持的实际出发来看,沩山老人的这一开示,至今仍有重要的现实意义。今日寺院之所以要坚持朝暮二课,月二依时布萨,其目的乃在于护持二众,使之不退转于菩提。
沩山老人非独提出了丛林修持中的悟道与护持的见地,更重要的是他还提出了行“水牯牛”道式的大菩萨行之主张。说起“水牯牛”,人们也许会与前面所说的“牛喻”相混淆。其实不然,沩山这里所说的“水牯牛”行,实质上与其沩山的师叔南泉之说有些相似。南泉普愿一次上堂云:“王老师自小养了一头水牯牛。拟向溪东牧,不免食他国王水草;拟向溪西牧,亦不免食他国王水草。不如随分纳些些,总不见得。”又云:“今时师僧须向异类中行”[一九]。南泉所说的“水牯牛”,大致有护持禅修之意;而后面的“向异类中行”,则大有修得正果后乘愿再来度生之意,它正好与沩山的“水牯牛”之见契合。《沩山语录》载沩山在示寂前上堂云:
老僧百年后向山下作一头水牯牛,左肋下写五字,云“沩山僧某甲”。当恁时,唤作沩山僧,又是水牯牛;唤作水牯牛,又是沩山僧。毕竟唤作甚即得? [二○]
若站在凡夫见地上来看,或许会认为沩山在这里真的堕入了下三道;殊不知沩山此乃“向异类中行”,他“虽行畜牲行,不受畜牲报”。实质上,沩山指的是行大乘菩萨行,他是要舍弃已证的涅槃位而乘愿再来此土度化众生。只有识得此意,才真正识得“沩山水牯牛”。
从沩山的开示学人修禅的阶次来看,沩山的禅教并不像有的学者所说的那般“杂乱”而无特色。要知道,若非一代大德,是断乎不可以住持沩山道场,且使其丛林具有十方所未曾有的宏大规模的。更何况沩山老人所开示的这一禅门修学阶次(悟道──见道──护持──水牯牛),非特适应于十方一切丛林,而且对于今天的佛门修持,也仍有十分重要的借鉴意义。
时西元二○○五年十二月十八日作于长沙北郊之落霞居
[一]参见《大正藏》卷五○页三四二下。
[二] 参见《大正藏》卷八五页一二八九中。
[三]《五灯会元》卷三《百丈传》载:“忽有一僧闻鼓鸣,举起钁头,大笑便归。师(百丈)曰:‘俊哉!此是观音入理之门。’师归院,乃唤其僧问:‘适来见甚道理便恁?’曰:‘适来肚饥,闻鼓声,归吃饭’师乃笑。”
[四]《五灯会元》卷三《南泉传》载:“师(南泉)在山上作务,僧问:‘南泉路向甚处去?’师拈起镰子曰:‘我这茆镰子,三十钱买得。’曰:‘不问茆镰子,南泉路向甚处去?’师曰:‘我使得正快。’”
[五]参见《大正藏》卷四七页五七八中。
[六]参见《大正藏》卷四七页五七八下。
[七]参见《大正藏》卷四七页五八二中。
[八]参见《大正藏》卷四七页五七九下。
[九]参见《大正藏》卷四七页五七八下。
[一○]又作“鹅王别乳”。《祖庭事苑》卷五载:置水与乳于同一容器,鹅王唯饮乳汁,而留下水。这里的水,表众生(凡);乳,表示佛(圣)。此鹅王别乳的故事是比喻觉者虽住于污秽之世间,亦不被污染,又喻指能辨别真伪正邪善恶。《法华玄义》卷五以鹅王比喻菩萨,谓无明乃同体之惑,如水中之乳,唯有登十住位以上菩萨之鹅王,方能饮无明乳,清法性水。
[一一]参见《大正藏》卷四七页五八三下。
[一二]大珠慧海《诸方门人参问语录》载:“有源律师来问:‘和尚修道还用功否?’师曰:‘用功。’曰:‘如何用功?’师曰:‘饥来吃饭,困来即眠。’曰:‘一切人总如是,同师用功否?’师曰:‘不同。’曰:‘何故不同?’师曰:‘他吃饭时不肯吃饭,百种须索;睡时不肯睡,千般计校。所以不同也。’律师杜口。”
[一三]参见《大正藏》卷四七页五八○中。
[一四]参见《大正藏》卷四七页五八一上。
[一五]参见《大正藏》卷四七页五七七下。
[一六]参见《大正藏》卷四七页五八○下。
[一七]见《五灯会元》卷四,《卍新纂续藏经》卷八○页八九上。
[一八]会昌法难一事,新、旧《唐书》载之颇详。本文所依为《旧唐书》卷十八中的《武宗本纪》。
[一九]均见《五灯会元》卷三《南泉本传》,《景德录》卷八《南泉本传》所载亦同。
[二○]参见《大正藏》卷四七页五八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