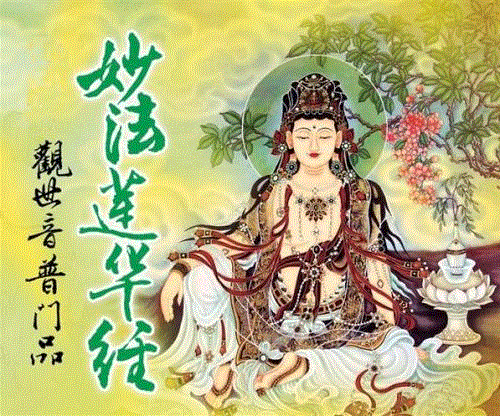藏传佛教寺院教育的发展历史及其特质
发布时间:2024-08-27 02:49:19作者:法华经全文网藏传佛教寺院教育不仅有着悠久的发展历史,而且具有与众不同的诸多特质,它在藏族传统教育史上占有特殊而重要的地位,甚至可以断言,寺院教育曾在藏族历史上完全垄断过藏族社会的整个文化教育。
一、寺院教育的发展演进历程
藏传佛教寺院教育,最初是伴随佛教的传播而产生,后来随着藏传佛教的兴盛而发展。寺院教育大致经过了初创时期、中兴时期和发展时期三个不同的发展演进历程。
1、初创时期
藏传佛教寺院教育初创于8世纪,桑耶寺则是开端“寺院教育”的第一座藏传佛教寺院,迄今已有1200多年的悠久历史。[1]在桑耶寺内设立译经院、讲经院和修行院等传播或修习佛教的专门学院。根据《巴协》记载:在桑耶寺大殿四周建有四大洲八小洲之称的学院或佛殿,如东边有清净律藏院(Rnam Dag Khrima Khang Gling)、智慧文殊院(Mkhyen RabVjam Dpal Gling)、妙音语言院(Brdv Sbyor Tshang Mang Gling),南边有降魔居士院(Bdul Vdul Sngags Pa Gling)、圣大悲观音院(Avry Pa Lovi Gling、译经天竺院(Sgra Bsgyur Gling),西边有毗若遮那院(Bee Ro Tsa Na Gling)、弥勒院(Byams Pa Gling)、禅定院(Bsam Gtan Gling),北边有聚宝院(Rin Chen Sna Tshogs Gling)、菩提发心院(SemsBskyed Byang Chub Gling)、护法贝哈院(Dkor Mdzod Dpe Har Gling)。[2]从当时桑耶寺各个学院所发挥的作用来看,每个学院皆凸现了各自的专业侧重点,如清净律藏院主要用于讲经或出家僧尼受戒的场所,藏族“七觉士”就是在这里受戒出家,成为吐蕃第一批比丘僧团;[3]智慧文殊院是研习佛学的场所;妙音语言院是学习多门语言的场所;降魔居士院是专门举行密宗法事的场所;圣大悲观音院是赞普赤松德赞修持本尊马头明王的场所;译经天竺院是专门翻译佛经的场所;毗若遮那院是授记预言的佛殿;弥勒院是预测未来的佛殿;禅定院是专门坐禅修炼的场所;菩提发心院是高僧大德讲经和出家人修行发菩提心的场所。
桑耶寺成为吐蕃王朝的宗教活动中心、文化教育中心,更是翻译佛经的重要场所。当时赤松德赞从天竺、唐朝等地邀请许多佛教学僧和高僧大德到吐蕃,并偕同吐蕃本族的学僧一起在桑耶寺译经院从事佛经翻译,在《桑耶寺简志》[4]中有具体描述。
特别是寂护在当时主持并讲解翻译律藏经典和中观思想,从而在吐蕃开创了讲经听法的学风。正如“静命堪布负荷讲说从律藏到中观的说法重任,打开讲听之风。”[5]这是注重对佛教显宗理论学习的一种重要举措。另外,根据《如意宝树史》记载,寂护在桑耶寺译经院主持译经的同时,在桑耶寺清净律藏院传授别解脱律仪戒,在菩提发心院传授菩萨戒,宣讲自己的《中观庄严论》和智藏的《中观二谛论》,建立了佛教显宗中观思想的主导地位。
2、中兴时期
藏传佛教寺院教育经过初创时期,便遭遇朗达玛灭法运动而彻底中断,后来随着藏传佛教“后弘期”的肇始而复兴,特别是噶当派高僧对寺院教育的兴起做出了巨大贡献。1073年,噶当派高僧俄勒贝喜饶(Rngog Legs PviShes Rab)在拉萨以南、聂塘以东的地方(今堆龙德庆县境内)创建一座寺院,最初叫桑浦乃托寺(Gsang PhuSne Thog Dgon),后简称桑浦寺。当时桑浦寺以弘扬藏传佛教因明学及佛经辩论而著称于整个藏传佛教教育界。俄勒贝喜饶是阿底峡尊者的四大弟子或三大弟子之一,曾赴康区亲近赛尊(Se Btsun)大师,深入学习佛教三藏,学业圆满后,于1045年返回前藏,建立讲经院,培养了众多学僧弟子。阿底峡尊者在聂塘传授佛法期间,俄勒贝喜饶遂前往阿底峡处听讲不少佛经,还请阿底峡和那措译师翻译了《中观心论注》(Dbu Ma Snying Povi Ti Ka),复请阿底峡撰写了《中观教授论》。他建造桑浦寺后,经常往返于热振寺与桑浦寺之间,沟通关系、交流经验,共同弘扬阿底峡的教法体系。俄勒贝喜饶去世后,由他的侄子兼著名弟子俄罗丹喜饶(Rngog Blo Ldan Shes Rab)继任桑浦寺住持。
俄罗丹喜饶(1059-1109),从小跟随俄勒贝喜饶叔叔学习佛法,由于他天资聪慧,深得叔叔喜爱,17岁时便派往克什米尔求法,途经阿里时又巧遇并参加了著名的阿里丙辰法会。[6]俄罗丹喜饶在阿里得到孜德王(Mngav Bdag Rste Lde)的儿子旺秀德(Dbang Phyug Lde)的资助,使他在克什米尔专心留学达17年,广拜名师系统研习佛法。留学期间曾应旺秀德的请求,同班智达噶丹嘉布一起翻译了《量庄严论》。俄罗丹喜饶学成返回故乡后,依然拜师学法不辍,还曾赴尼泊尔拜阿都拉亚巴寨等大师专门修习密法。从尼泊尔归来,俄罗丹喜饶开始校订或翻译佛经,成为一名著名的佛经翻译家。同时,他以桑浦寺为中心在拉萨、桑耶、聂谷那、聂岗土、藏绛喀等地,讲经说法,广收徒弟。他主要传授因明学、慈氏五论、中观等佛教显宗经论,其学僧弟子逐渐达到23000多人,其中能够宣讲佛法的有2130多人,阐释经论的有1800多人,讲解量决定论的有280多人,讲授量庄严论等大经的有55人。1109年,俄罗丹喜饶在桑耶寺附近的旅途中去世,享年50岁。在数万名徒弟中有四大著名弟子,即香蔡邦曲吉喇嘛(Zhang Tshe Spong Chos Kyi Bla Ma)、卓罗巴洛智琼奈、琼仁钦札和寨喜饶帕。这四大弟子继续弘扬俄叔侄开创的桑浦寺教法体系,即因明学和辩经学,在藏传佛教寺院教育中得到蓬勃发展。
香蔡邦曲吉喇嘛主持桑浦寺期间,学僧猛增,寺院扩建,寺院教育趋于完善。当时以俄罗丹喜饶灵塔为中心,在东边由恰巴曲吉桑格(Phya Pa Chos Kyi Seng Ge)讲授因明学、在南边由嘉强日瓦(Rgya Mching Ru Ba)讲授般若、在西边由仁钦次臣(Rin Chen Tshul Khrims)上师讲授现观庄严论、在北边由云丹喜饶(Yon Tan Shes Rab)讲授律藏。[7]特别是恰巴曲吉桑格将因明学分类分科并根据学僧的佛学水平分成五个班级,而且建立相互提问解答的辨经制度,使藏传佛教因明学或辩论学更加科学化。这一时期除了桑浦寺外,还有不少寺院初步建立了学习五部大论的教学机制,诸如蔡贡唐(Tshal Gung Thang)、德瓦坚热瓦堆(Bde Ba Can Ra Ba Stod)、纳唐(Snar Than)、萨迦(SaSkya)、昂仁(Ngam Ring)、夏鲁(Zha Lu)、楚普(Khro Phu)、奈宁(Gnas Rnying)、矫摩隆(Skyor Mo Lung)、布东(Bo Dong)、巴南嘎东(Pa Rnam Dgav Gdong)、堆隆措麦(Stod Lung Mtsho Smad)、斯普(Zur Bu)、桑日(Bzang Ri)、泽当(Rtsed Thang)等20多个学经院,[8]则是为积极推行学习五部大论、建立健全寺院教育体制做出重要贡献的寺院。[9]至此,藏传佛教后弘期内产生的以桑浦寺为中心的藏传佛教寺院教育体制基本形成。
3、发展时期
随着藏传佛教寺院的蓬勃发展,寺院教育在藏族地区日臻完善,特别是后起之秀格鲁派的创立,大大促进了寺院教育的长足发展。1409年,宗喀巴大师在拉萨以东的卓日窝切山腰创建了甘丹寺,并在该寺推行严守佛教戒律,遵循学经次第,提倡先显后密即显密相融的佛学体系,并成功地建立了有章可循的寺院机制和一整套严格的教学体制。实际上,宗喀巴早在他36岁时就开始招收徒弟讲经说法,先后在各地讲授《现观庄严论》、《因明》、《中论》、《俱舍论》等;还专门研习噶当派的教法及《菩提道炬论》等重要经论,同时系统修学萨迦派的“道果法”、噶举派的“大手印法”等各种密法。因此,宗喀巴最终通达各派显密教法,以中观为正宗,以噶当派教义为立宗之本,综合各派之长,并亲自实践或修行为证验,建立了自己的佛学体系。格鲁派在继承桑浦寺寺院教育的基础上,创造性地发展了藏传佛教寺院教育。比如,宗喀巴不仅富有创见性地将五部大论有机地结合在一起,而且在格鲁派寺院内建立了学科分类、高低分层的教学体制,寺院教育更加系统化。具体而言,宗喀巴根据五部大论的相互关系和内容深浅不同等特点,制定先学摄类学,认为摄类学或释量论是开启一切佛学知识之门的钥匙;其次为般若学,认为般若学是佛学的基础理论;之后为中观学,认为中观学是建立佛学观点的理论基石;而后为俱舍论,认为俱舍论是领会小乘之因、道、果理论的权威经典;最后是戒律学,认为戒律学是了解和遵循佛教戒律学的历史和规则,以及如何修持和授受佛教戒律的经典理论。可见,宗喀巴在融会贯通五部大论的基础上建立的教学方法,是一种系统掌握佛教三藏的颇具科学性的寺院教育体制,在藏传佛教寺院教育史上具有创新性。所以,这一教学体制很快在格鲁派各大寺院推行,并对其它宗派的寺院教育产生深远影响。这是宗喀巴对藏传佛教寺院教育事业做出的突出贡献。
二、寺院教育的模式及内涵特质
藏传佛教寺院教育具有与众不同的独特风格,无论从教育模式、学科内涵,还是在学位制度等方面皆有自己的显著特质,其特质主要反映在教材、教学和学位三个方面。
1、教材
就一般而言,佛教五部大论[10]是藏传佛教寺院教育中的主要教材。因为五部大论涵盖了佛教三藏。[11]值得提出的是,五部大论在佛教显密二宗中纯属佛教显宗理论,它不过多涉及密宗实践修持内容。五部大论最初是在后弘期兴起的藏传佛教六大显宗学院中开始全面学习,逐渐成为主要教材。这六大显宗学院分别是桑浦寺、德瓦坚热瓦堆扎仓、蔡贡唐寺、巴南嘎东寺、矫摩隆寺和斯普寺,后来格鲁派寺院继承这一学风,并得以发扬光大,至今五部大论依然是各个寺院教育中无可替代的重要教材。
藏传佛教认为,印度古贤二圣六庄严[12]是全面继承和严格遵循释迦牟尼佛法的无与伦比的八位杰出论师,他们的有关论著则是最具权威的佛学经典论著。所以,五部大论中的因明学以陈那和法称的论著为准、中观学以龙树师弟的论著为准、俱舍论以无著兄弟的论著为准、戒律学以释迦光和功德光的论著为准。同时,系统学习二圣六庄严的经论,还意味着最终实现树立佛学中观思想的宗旨。
从佛学见、修、行的角度看,大乘之“见”是在中观学和因明学中阐述或体现,而大乘之“行”则在般若学中阐述或体现;小乘之“见”和“行”都在俱舍论中阐述或体现;大小乘之共同戒律是在戒律学中阐述或体现;而大小乘之“修”则在 “见”和“行”的阐释中涉足。

根据格鲁派的阐释,释迦牟尼开创的佛教正法,归根结底,是由教义理论和实践证验构成,因而一切“教”的正法,则摄在经、律、论三藏之中;一切“证”的正法,又摄在戒、定、慧三学之中。为此,提倡三藏不可偏废,而三学又必须全面修习。也就是说,凡是立为佛教正法者,其见、修、行三者不可违背三藏教法;自心行持,也要随顺三学证法。同时,还要具备方便智慧双运之道,以及空性大悲之觉悟。正因为有了如此的宗教见地,方令每个学僧力争做到对于经藏,多闻深思,在大小乘的三学上,认真修习;对于律藏也要尽力修习,通达戒、定二学;对于论藏也要不断研习,获取通晓诸法性相的智慧。特别是戒、定、慧三学在寺院教育中成为必须遵循的三条修习佛法的途径,其中缺一不可。为此,制定出具体的教学内容即教材,如在戒律学方面,主要学习《律经》;在定学方面,重点学习《现观庄严论》;在慧学方面,主要学习《中论》、《因明学》、《俱舍论》。在寺院教育中之所以对佛教三学极为重视,自有其道理,认为三学中的戒律学是佛教的根本,是修法的基础;而定学是约束自心、避免散逸的途径;慧学就是增长智慧、不昧于解脱之道。故有无戒不定,无定不能生慧之说。这便是藏传佛教寺院教育中竭力系统研习五部大论的重要因素。
2、教学
藏传佛教寺院教育在教学方式上也有自己的独特风格,以格鲁派六大寺院之一的拉卜楞寺为例,该寺按照佛教显、密宗的分科原则,在寺内设立六个学院,即闻思学院、续部下学院、续部上学院、喜金刚学院、时轮学院、藏医药学院。除了闻思学院外,后五个学院可纳入密宗范畴。然而,学院中规模最大、学僧最多的则是闻思学院,即显宗学院,其内部分设13个不同的学科班级,整个学期最少也在15年以上。显宗学院主要学习佛教五部大论,重在全面理解和深刻领会。也就是说,每位学僧通过师授、背诵和辩论的形式,渐次精通佛教《因明》、《般若》、《中观》、《俱舍论》、《律学》五部大论。
特别是辩论和背诵是藏传佛教寺院教育中最具特色的学习方法,通过辩论可提高学僧的哲学思辨能力,从而能够进一步领会藏传佛教的深奥义理。就一般而言,背诵经文和辩论佛学疑难问题,则是藏传佛教寺院教育中的两大行之有效的教学方式。因此,在各个寺院学习的年轻僧人,尤其是藏传佛教格鲁派学僧将自己的主要精力放在背诵经文和辩论佛学疑难问题之上。比如,他们在寺院日常生活中将早晚的时间主要用于独自背诵经文,而早晚背诵的经文又成为参加上午或下午集体辩论佛学疑难问题时广为应用或印证的理论武器。所以,背诵经文和辩论佛学难点已成为藏传佛教寺院教育中相辅相成的两大学经方法,犹如一车之两轮,缺一不可。实际上,这一学经方式的形成,主要取决于藏传佛教寺院的考试制度。如寺院考试制度不但严格而制度化,而且与众不同,具有自己的独到之处。其中背诵经典考试和辩论考试,则是寺院教育考试的主要方式。如在背诵经文的考试中,背诵的经典越完整、篇幅越长,其考试成绩就更加优异;辩论考试是以正方或反方的形式进行辩论,在藏传佛教的宗教术语中被称为立宗辩论,就是围绕某学说或论点进行答辩,提出其中的许多疑难问题,让答辩人一一解答或简明扼要的阐释,如对答如流或阐释深入浅出,其答辩人的辩论考试及格或成绩优异,否则,其答辩考试不能通过,需要重新复习,有待补考。尤其是这一考试方式从低年级就纳入僧人的学经之中,并对学僧的学习起到促进作用。由于藏传佛教经院教育提倡并重视辩论这一学经方式,每位学僧个个思维敏捷或善于辩论,并具有超常的哲学思辨能力。
总之,在显宗学院学习的学僧,其学习过程则是广闻博学,背诵强记,多维思考,反复辩论,从而达到对“五部大论”的娴熟理解和融汇贯通,最终顺利考取格西学位,并进入密宗修习阶段。密宗修习的年限无期,主要取决于学僧的勤奋、智慧、悟性等个人条件来不断提升或获得成就。
3、学位
藏传佛教格西(Dge Bshes)[14]学位,是随着寺院教育的不断发展而逐步建立起来的一种宗教学位制度。格鲁派三大寺没有创立之前,在藏传佛教教育界已经产生授予格西学位的教学体制,而且有不同级别的格西学位称谓,如热绛巴(Rab Vbyams Pa)、噶西巴(Bkav Bzhi Pa)、噶俱巴(Bkav Bcu Pa)等格西。在五部大论中只精通般若学后可考取热绛巴格西学位,五部大论中学完除了因明学外的其它四门学科后可考取噶西巴格西学位,学完五部大论后可考取噶俱巴格西学位。后来在拉萨创建格鲁派三大寺,使授予格西学位的制度日臻完善,尤其是第四世班禅罗桑却吉坚参在代理甘丹寺赤巴(法台)期间,在拉萨传昭大法会上创立了授予拉然巴(Lha Ram Pa)格西学位的制度。[15]
除了拉然巴格西之外,还有许多不同级别或专业的格西学位,诸如“措然巴”(Sthogs Ram Pa)、“林赛巴”(Gling Gsal Pa)、“多然巴”(Rdo Ram Pa)、“阿然巴”(Sngags Ram Pa)、“曼然巴”(Sman Ram Pa)、“噶然巴”(Bkav Ram Pa)等。
措然巴格西,是仅次于“拉然巴”的一种格西学位。每位考僧在拉萨小昭寺举行的大法会上,通过拉萨三大寺众高僧前答辩佛教经律论后,才能获得这一宗教学位。
林赛格西,该学衔排在措然巴格西之后,是某位学僧在拉萨三大寺中的任何一寺内通过答辩佛教经论而考取的一种格西学位。
多然巴格西,是某位学僧在各大寺院大经堂门前的石阶上举行的法会上通过众僧前答辩佛教经论而获取的一种格西学位,排在林赛格西之后。凡是具备条件的各大寺院均有资格授予多然巴格西学位。
阿然巴格西,是某位学僧在各大寺院的密宗学院中通过对密宗理论的研习以及实践修炼而获得的一种格西学位。一般而言,进入密宗学院修学的条件比较严格,其学僧必须先经过在闻思学院研读藏传佛教五部大论的阶段,并在此获得毕业后才有可能升入密宗学院深造;最好是取得上述格西学位中的任何一项后,被选派或推荐到密宗学院研修,最后取得阿然巴格西学位。阿然巴格西中也有等级差别,如在拉萨上、下密宗学院中获取的阿然巴格西,是至高无上、最为权威的密宗格西学位。
曼然巴格西,是某位学僧在藏传佛教各大寺院的藏医学院长期研习藏医药学而获得的一种格西学位或藏医学位。由于藏医学院所学理论知识极为广泛深入,而且还要经常进行在野外采药等实践,故其研习时间相对较长。
此外,许多藏传佛教寺院中还授予“噶然巴”(Bkv Ram Pa)、“热绛巴”等级别较低的宗教学位,在此不一一赘述。
总之,考取宗教学位,是每一名出家僧人的一大宿愿,也是显示自己佛学知识水准的主要头衔。然而,藏传佛教寺院教育中的格西这一宗教学位并非人人能够考取,而是极少数僧侣经过长期勤奋修学才有机会获取。一旦获得格西学位,特别在大昭寺举行的大考场通过“拉然巴”格西学位的考试,在藏传佛教界具有很高的荣誉和宗教地位。因为拉然巴格西,是藏传佛教格西学位中级别最高的宗教学位,也是藏传佛教显宗中最权威的学衔。
三、结语
综上所述,藏传佛教寺院教育经过了一个循序渐进、不断创新、逐步完善的发展历程,它作为一种教育模式,更具有诸多与众不同的特质。藏传佛教“前弘期”作为寺院教育的初创时期,围绕佛经翻译开办了讲经说法的学院;而“后弘期”作为寺院教育的中兴时期,随着因明学的兴起而形成了研习五部大论的学风;至宗喀巴时代作为寺院教育的发展时期,伴随格鲁派三大寺的创立而建立了系统学习五部大论的教学体制。尤其是寺院教育特有的教育资源、教学方式、学科内容、考试规则和学位制度,从不同角度反映了藏传佛教高度发达的培养贯通佛教三藏的高僧大德的教育体系。可以说,藏族地区的数千座寺院既是信仰和传播藏传佛教的摇篮,又是继承和发展藏传佛教文化的学府。